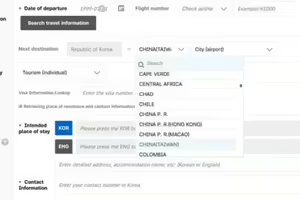早上七點多,我正一個人驅車在郊外遊蕩。一個陌生的號碼打了進來,這驟響的鈴聲韌性十足。我接起電話,對面傳出一個甕聲甕氣的女聲。“你是某某嗎?猜猜我是誰?”
她執著地讓我猜,直到我快失去耐心的時候,才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小名:五丫頭。聽到這個名字,我眼前立即浮現出一個畫面:夕陽下,一個髒兮兮的小女孩,翹起的髮辮在晚風中飛揚,她將手中的小皮鞭用力一揮,在半空中劃出一道輕快的弧線。
記憶中的小姑娘,是我多年來一直思念的表姐,如今卻怎麼也無法和這個甕聲甕氣的女聲聯繫起來。
1
五丫頭是我三姨家的表姐,比我大三個月。在我五歲到十一歲的時候,母親每年都會在寒暑假時,將我從居住的小城,千里迢迢地送到三姨家住上一個多月,說是為了鍛煉我的自理能力。
從我懂事起,就沒見過三姨。她在生了六個女孩之後,終於如願得了個男孩,結果孩子生下來當天,三十八歲的她也因大出血過世了。剩下六個表姐和一個表弟,和姨夫一起艱難度日。
六個表姐的小名一概以丫頭和排行來稱呼。五丫頭排行老五。
我家雖然只是在內蒙古的一個小城裡,對打小生活在農村的表姐們來講,卻是毋庸置疑的“城裡人”。這種落差在年齡相仿的姐妹們眼裡,表現得尤為明顯。
當時四丫頭比我大三歲,五丫頭和我同歲,六丫頭比我小一歲。年紀相仿的幾個人瘋在一起的時候,好得恨不能合成一個人;生氣的時候,也打得不可開交。其中五丫頭最為強勢。
小時候的五丫頭,頭髮稀疏焦黃,梳著兩個小辮子,有著細長的眼睛和高而亮的額頭。我上三年級的時候,她已經不上學了。三姨夫買了幾頭小豬,她就和鄰居小女孩一起每天出去放豬。五丫頭說話不但語速快,還喜歡眨巴眼睛。趕豬的時候,奶聲奶氣地大喊一聲:“咯咯咯!”
五丫頭勤勞、能幹,總是計算著養多少頭豬才能幫姨夫賺到錢。別的孩子對做農活喜歡偷懶,但她從來風雨不誤,且將各類農活都做得有模有樣。
2
我的母親乾淨俐落,冬天送我去三姨家的時候,會給我準備好由綠色帆布和棕色翻毛組成的小皮鞋,戴一頂鑲了白兔毛的小帽子。這樣的行頭,即便在我家也是要穿戴好幾年的。而五丫頭和表姐們都穿著大表姐手工縫製出來的棉鞋,常常穿不了多久,鞋幫就變成鞋底了。
一天早晨,五丫頭趁我還沒起床,全副武裝地穿走了我的行頭,連外衣都沒放過。午飯過後她回來,衣服已髒得面目全非——她穿著去和村裡的男孩子們滑冰車了(坐在一塊小木板上,半個屁股坐在冰上往 下滑) 。
三姨夫氣急之下,拿起炕上的笤帚,劈頭蓋臉地打了她。她坐在地上蹬著腿使勁哭,眼睛怒視著我。
黃昏的時候,表姐和姨夫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在炕上翻一本小人書,五丫頭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突然把我按在炕上打了一頓。記不清哭了多久,正巧四姨家的三表哥來找我,見我被欺負了,很是氣憤,拉著我恨恨地往出走,對五丫頭說“你等著!”
過了一天,三表哥送我回三姨家的時候,五丫頭正在炕上呼呼大睡。兩個又細又長的辮子垂在一側。見屋裡沒人,三表哥從櫃子上拿起剪刀爬到炕上,兩下就將五丫頭的辮子剪了下來,然後拉著我跑了。
晚上回去的時候,五丫頭披頭散髮地坐在牆角,眼睛紅紅的,顯然是哭過了,身邊放著那兩條可憐的小辮子。我心生憐憫,爬到她身邊,從頭上拿下兩條打成蝴蝶的絲帶遞給她,這兩條紅絲帶是她一直想得到的。
我說:“送給你。”她撇撇嘴,很不買帳,“我沒辮子了,不要!”嘴上說著,卻把紅絲帶攥在了手裡。
3
我們當然也有很要好的時候,那時候,她走到哪裡都拉我一起。
夏天,我們最大的樂趣是去村外的一個大池塘邊玩。那裡綠樹成蔭,溪水潺潺。林間的空地上,開滿了很多雜色的小花,還有大片大片的蒲公英。蒲公英開過的時候,我們將白色的絨球從根上掐斷,迎風一吹四處飄散,是童年最好的遊戲。
因為沒有生母照顧,加上做的農活多,她的衣服常常髒得發亮。而五丫頭和我一起時,最愛玩的遊戲就是剪刀石頭布,只要我輸了,就要給她洗衣服。
一次,我們在池塘邊玩剪刀石頭布,那次我贏了,她不甘心,就去找胖丫(和她一起放豬的鄰家女孩)。胖丫輸了,就用一根長長的木條、挑著五丫頭的褲子,在池塘裡攪了一會,然後將它曬在了樹杈上。因為池塘底下有很多泥漿,等五丫頭褲子幹了的時候,汙塗塗、硬邦邦的,都能在地上豎起來,即便這樣她也很滿意。
那天,五丫頭很高興地坐在草地上,用毛毛草編小貓給我們,她的手很靈巧,編出很多小動物,惟妙惟肖。
那次我們比平時回家晚了很多,卻看見了火一樣燃燒著的落霞。夕陽下的大地碧綠而蔥郁,水一樣潔淨的長空上飄著層層的雲朵。西方的天幕上,即將落下的太陽像個大火球一樣靜靜地燃燒。
夕陽下,五丫頭滿身霞光,趕著十幾頭小豬走在前頭,歡快地在金色的柔光裡跳躍,竟出奇的美麗。以致近三十年過去了,那一幕依舊在記憶裡恍如昨日。
4
十二歲以前,夏天被送回鄉下是快樂的,因為田野就是最大的遊樂場,而寒假卻比較難熬。漫長的冬日,表姐妹們只能憋在屋子裡玩抓豬骨頭。
北方的冬天夜特別長,白晝卻很短。加上天氣寒冷,姨夫家家境不好,為了節約柴火,一般在晚上六點左右,小孩子們就都被趕上了床。
因為我是客人,晚上睡覺的時候,總是被三表姐多鋪了床被子摟在懷裡,以此為我取暖。而五丫頭一定要睡在我的旁邊,每次睡前都和我打鬧一會兒。直到有一天她們發現我會講故事,這爭鬥就變成了故事會。
那時每天睡得早,所以一般清晨五、六點,大家就差不多都醒了。這時候,五丫頭就會讓我講故事。
從《格林童話》到《聊齋》,常常一口氣講好幾個,口乾舌燥了,她們還興致勃勃。記憶裡,三姨家的炕好長,並排睡著十幾個小丫頭,鄰居家的孩子也會過來湊熱鬧。
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五丫頭已經不上學了,而其他的表姐,也都沒讀過什麼書。三姨夫的原則是:農村的女孩子,總是要嫁人的,讀書沒用。
因此在表姐妹們的眼裡,能講那麼多故事還能認許多字的我,是值得羡慕的,她們也會因此更加厚待我。
其它的表姐們自不必說,連一向喜歡和我作對的五丫頭,也常常會將一些得來不易的好吃的,比如一個小番茄、一個香瓜,緊緊捂在口袋裡很久,常常捂得溫熱,最後送給了我。那份情誼,幼小的我不是沒有感覺,只是不懂得表達。
快樂的時光似乎很快就結束了。我十三歲的時候,鰥居多年的三姨夫給表姐們找了個後媽,從此母親再也沒送我回去過。而那時,儘管痛徹心扉地想念她們,但苦於通訊極不發達;開始還有書信來往,也都是我寫給她們,她們因為不會寫字而從不回復。
我們慢慢失去了聯繫,以致最後杳無音訊。
準備上高中的時候,我偶然聽說五丫頭已經結婚了。而且為三姨夫養豬賺了很多錢,特別能幹。
二十多年過去了,和我同齡的五丫頭,不但有了一雙兒女,她的女兒也已經結了婚。她也從當年的小村莊遠嫁到了另一個村子,日子雖比當年好了很多,但靠天吃飯、依舊辛苦。
我想去看她,她卻怎麼也不肯說出她的地址。
她說,她這輩子從小就在我面前自卑,小時候因自卑可以欺負我,現在欺負不了了,也就不想再見我了。千辛萬苦地要到我的電話,就是為了聽一下我的聲音,因為這麼多年真的太想念了。
她怕我看見她的貧窮,更怕我看見她的衰老、以及幾十年沒變而延續下來的生活。她說,二十年裡,她記憶中最深刻的就是我頭上飄揚的發帶,還有每天清晨給她們講故事的聲音。
我和童年最好的朋友,卻終究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