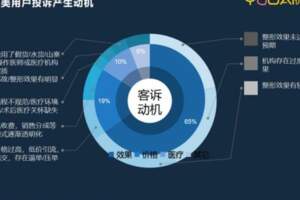來源:ladymax
奢侈時尚品牌最近掀起了一股動物迷戀。
如果說Burberry的牛年新春系列只是一年一度的例行生肖主題,那麼Loewe與日本動畫電影《龍貓》、Gucci與哆啦A夢的最新聯名系列,Givenchy新晉創意總監Matthew Williams 2021春夏系列中小惡魔羊角帽和羊角高跟鞋,以及《Vogue》義大利版1月份最新封面以動物為主題,足以說明奢侈時尚行業正心照不宣地迎合著某種趨勢。
在國內時尚行業,MO&Co.米奇聯名和兔八哥系列,DAZZLE的藍精靈和阿童木系列,Broadcast播的哆啦A夢和SNOOPY系列,太平鳥的芝麻街和寶可夢聯名等眼花繚亂的IP合作系列,眼下也已經成為各個品牌最賺錢的系列。
而大量的問題湧現了出來。
Matthew Williams為何在沒有任何語境的情況下,為Givenchy首個系列推出動物羊角元素?以工藝和皮具著稱的西班牙奢侈品牌Loewe推出動畫聯名系列,是否代表了這個傳統奢侈品牌的巨大策略轉變?Gucci的注意力從真實的動物元素轉向了卡通IP暗示了何種內在態度轉變?卡通IP聯名系列為何尤其在中國市場屢試不爽?市場的過熱之後這種簡單直白的創意形式是否具備任何可持續性?


奢侈時尚品牌最新掀起的一股動物迷戀,背後是文化和商業影響下的社會心理變化
這些覆蓋了文化和商業的問題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但是當奢侈品牌開始選擇與面向大眾的服飾品牌相同的卡通聯名對象時,重新審視當下的市場變得尤為緊迫。
事實上,對於動物和自然世界的好奇心在時尚界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除了古代服飾在刺繡和圖案中對自然元素的體現,現代時裝對此議題的探討或許可追溯至1937年Elsa Schiaparelli的龍蝦裙。能夠將龍蝦突然堂而皇之地印在正裝裙上,本質上是拜彼時活躍的當代藝術所賜。龍蝦裙打破了服飾單調的實用屬性,讓時裝設計師早期的裁縫角色沾染上了藝術家的光芒。

Elsa Schiaparelli 1937年推出的龍蝦裙
1917年杜尚的小便池《泉》影響了之後一個世紀的文化歷史,它第一次質疑了何為藝術品的傳統藝術觀念。作為這種思潮的附屬品,時尚也開始擴展邊界,探討何為時尚的命題。時裝從這時起不再只是衣服,而被賦予戲謔的底色,成為了文化符號和想像力的畫布。
英國V&A博物館在2018年開幕的Fashion from Nature《源於自然的時尚》展覽呈現了時尚從自然界中汲取靈感的種種案例,最近該展覽也來到了深圳。在展覽的時間線上,人們看到時裝設計師一貫在自然界尋找靈感,從而用特殊材質模仿了動物的形態,表現出對仿生學的興趣。動物的紋路如豹紋、斑馬紋已經成為了一種常見的經典印花,奢侈品牌對於動物皮草的運用在過去的數十年極為普遍,不過近年來由於動物保護組織的反對而逐漸謹慎。
任何時裝愛好者都可以隨意想到時裝設計師運用動物形象的案例,Alexander McQueen對於動物羽毛和海洋生態的探索可謂經典,相對商業化的Thom Browne將獵狗包打造成爆款,並在2014年秋冬的男裝秀中打造了大象、兔子等動物頭飾。

Alexander McQueen 2010春夏系列Plato's Atlantis
但是這種對於動物的迷戀在近年明顯發生了某種改變,Gucci是一個典型例子。
Alessandro Michele在2014年接手Gucci後,就因為品牌建立了一個包羅萬象的自然世界而著名。在這個階段,蜜蜂老虎蛇和「已然/未然」展覽中的花卉布景等自然元素成為了品牌的典型圖景。無數人在花卉布景前打卡展覽,掀起了品牌的第一波浪潮。由藝術家Johnyuyi拍攝的創意圖像在2017年的#TFWGucci數字創意互動項目中獲得了最多的贊,她在臉上畫上了一條代表了Gucci的蛇。
不過,從2017年春夏系列開始,Gucci似乎將注意力從現實自然世界轉移到動畫世界,品牌推出了首個唐老鴨系列,由此開啟了與迪士尼卡通角色聯名的傳統。
此後Gucci在米奇90周年之際推出了2020年初的米奇系列,因為恰逢中國鼠年,該系列達到了一石二鳥的效果。配合米奇主題紙袋,該系列在中國市場大受歡迎。與此同時,Gucci將卡通生肖系列作為了例行項目。2018年由兩隻波士頓㹴詮釋的狗年系列和2019年Gucci推出的「三隻小豬」新年特別系列都獲得了不錯的反響。最新推出的哆啦A夢系列證明Gucci要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
在第一個階段,Alessandro Michele用繁複的自然世界帶領Gucci征服了消費者心智,但是它仍然是舊時裝體系的延續。與Alexander McQueen等設計師一樣,Alessandro Michele保持著對自然的深刻好奇心,體現了詮釋和重現自然的動力。這種創作方式與Fashion from Nature呈現的很多作品是一致的,它們都將設計師對於自然的欣賞和好奇,通過二次加工體現在時裝畫布上。
然而進入第二個階段,唐老鴨、米奇、哆啦A夢等虛擬卡通角色加入了Gucci的動物園。這些角色省去了此前設計師詮釋自然的複雜過程,將IP形象剪切粘貼到成衣上,便可打包成為全新的商品。



近三年來唐老鴨、米奇、哆啦A夢等虛擬卡通角色加入了Gucci的動物園
這樣的現象背後,IP經濟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IP經濟已成為全球文化娛樂產業發展的新形態。文化IP以其優質原創內容聚合第一代粉絲,通過各種衍生方式來擴大粉絲群體。在這一過程中,IP的價值得以轉換、變現、放大並生態化。
迪士尼是全球IP經濟的標杆,旗下電影、遊戲、主題樂園、文創產品全部都是IP的衍生品,並且通過上述業務覆蓋了廣泛的消費者。而迪士尼公司年收入近700億美元的重要驅動力就來自於IP授權業務。
米奇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大生意。據《Fast Company》報導,米奇在1928年的動畫短片《汽船威利》中登場的5年內,每年的商品銷售就達到了100萬美元,相當於2019年的1900萬美元。除了來源於童話故事的經典動畫IP,迪士尼還收購了皮克斯影業、漫威影業和盧卡斯影業,因而擁有了《星球大戰》、《冰雪奇緣》、《飛屋環遊記》等動畫IP。
迪士尼成熟的IP授權模式和廣泛的受眾顯然為時尚品牌提供了極具吸引力的成熟條件。先是從千禧年後,很多潮流品牌和個別設計師品牌開始與迪士尼達成合作。
據Highsnobiety數據,迪士尼的聯名項目包括2009年與Supreme,2010年與CLOT、Vans和Stussy,2011年開始與COMME des GARÇONS旗下品牌開展數次合作,2016年與Kenzo和A Bathing Ape等。
在美學意義上,潮流品牌與動畫IP之間其實存在著天然的連接點。簡潔而張揚的圖案、明亮的色彩選擇,可供不斷複製傳播的符號,樂觀活躍並充滿奇思妙想的性格,架起了二者之間的橋樑。在商業上,潮流品牌的大眾屬性與動畫IP也十分契合。

Supreme與米奇2009年的聯名合作系列
當我們去看最早一批進行卡通形象聯名的品牌時,也不難看出這些品牌透露出的潮牌化苗頭,以及它們對於大眾市場的興趣。
2009年秋冬與米奇合作的Jeremy Scott向來以大膽童趣為標誌性風格。Givenchy 2017年與小鹿斑比Bambi的合作,體現出了Riccardo Tisci在任時期的Givenchy早期的潮牌化傾向。而永遠洞悉市場變化的Comme des Garçons則成為市場先鋒,最早讓嚴肅的高級時裝與大眾流行符號進行對撞。
接下來幾年中,Gucci作為黑馬征戰市場,依靠的是千禧一代的力量。品牌與千禧一代喜歡的說唱歌手合作,推出logo產品,熱衷於社交媒體互動,一直都體現著奢侈品牌潮牌化的傾向。從Gucci近期的動畫IP合作上,也可以看到奢侈品牌潮牌化的這條線索。
奢侈時尚品牌突然盯上了迪士尼,除了時尚文化向潮流文化靠攏,還因為動畫IP可以提供新鮮的商業刺激點。尤其和熟悉的卡通IP聯名,可以激起包括「回憶」、「認同」、「代入」等心理和情感動機。並且卡通系列通常沒有尖銳的立場,普適度較高,連接的多是快樂的回憶,不失為一張安全牌。
在奢侈品行業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動畫IP是奢侈品牌所能最快且最低成本獲取的創意素材。儘管授權費用可能不菲,但是品牌省去了漫長的消費者教育過程。在消費者對品牌審美疲勞的時期,品牌不斷用這類聯名合作填充空檔,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是一種非常直接的刺激銷售的手段。
這就是為什麼起初我們還能在這些聯名合作中找到一些邏輯,但近來如海洋般的聯名合作已經變得毫無邏輯,幾乎變成了品牌掘金的工具。
這也是為什麼儘管人們已經對聯名合作幾乎免疫,動畫IP產品依然奏效,在大眾市場賺得盆滿缽滿。更多國產品牌IP也正遵循迪士尼的道路,開始成為時尚品牌的素材庫。
不過,我們的探討不僅限於以聯名合作為表現形式的IP經濟,而應看到背後浩浩蕩蕩的符號化趨勢。不僅是動畫IP,人們越來越多地看到品牌對某種動物的反覆強調,Moschino大火的小熊圖案、Kim Jones為Dior帶來的卡通蜜蜂,亦或是卡地亞的獵豹、寶格麗的蛇,這些動物都成為了品牌的符號,是另一種logo。
當今的時裝設計從最早對自然的好奇,轉移到了對自然元素的利用與剝削,從最早那種精細的、需要解讀的創作形式,轉移到了一目了然、適於傳播的符號。時尚品牌對動畫IP的採用,是對文化的再生產,對碎片的去語境化打亂重組,這再一次證明Virgil Abloh的出現是時代的必然。
與此同時,當主張稀缺的奢侈品牌接納了迪士尼的包容性時,我們看到奢侈品作為一種以往被視為高級的文化,也沒有例外地成為了大眾消費品,大眾時代的來臨已是不爭的事實。
娛樂、童真和趣味取代了嚴肅批判。當下的時裝不再需要人們凝神研究的努力。
奧爾特加·加塞特在《大眾的反叛》一書中寫道,「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與舒適,但對於其原因一無所知,也沒有這個興趣。因為他們無法透過文明所帶來的成果,洞悉其背後隱藏的發明創造與社會結構之奇蹟,而這些奇蹟需要努力和深謀遠慮來維持。他們認為自己的角色只限於對文明成果不容分說的攫取,就好像這是他們的自然權利一樣。」
StyleZeitgest雜誌創始人Eugene Rabkin在一篇文章中表示,縱觀當代時尚史,關於時尚是否是一種藝術形式的爭論一直在反覆上演。但是現在是時候將這場辯論轉移到過去20年形成的新現實中去,時尚不是藝術,而成為了娛樂。
作者援引在1944年出版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中,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和馬克斯·霍克海默的觀點,他們將周圍看到的世界描述為一個由大規模生產和消費商品所驅動的世界,包括由所謂的文化產業所生產的文化產品。
這在時尚界中最鮮明的體現之一就是,如今的時裝愛好者對Raf Simons和Rick Owens感興趣,不是因為這些設計師創造了值得思考的美學世界,而是因為他們在自己喜歡的說唱歌手身上看到了他們的衣服。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時尚已經成為另一種文化商品。是的,時尚一直是一種商品,但不是單純的商品。回到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觀點,普通的文化消費者由於日常生活的過度勞累和壓力,並不會在藝術中尋找意義,而是去尋找娛樂,因為他們沒有精力和興趣去深入研究文化。藝術需要努力——關注、思考、教育。娛樂需要的只是你的錢。」
當然,在如此一個令很多人失望的世界中,我們還可以做出更具樂觀意義的解讀。
時尚界對於自然的狂熱或許可以視為對過去數十年盛行的人文主義的轉折。時裝文化長達三十年的極簡主義和解構主義,以及對於全球異域文化的組合、拼接與挪用,最終使人們進入了精神內核的空虛,無內容可供解讀和解構,只剩下一地的符號。Virgil Abloh之徒撿起地上的符號,不試圖探究任何意義。
《Vogue》義大利版主編Emanuele Farneti在一月刊編者言中解釋道,動物特刊封面的初衷在於,告訴人們地球並不是圍繞人類而存在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向原始自然回歸不失為一種救贖,尤其在當下的疫情之中,社會心理需要的僅僅是自然的療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