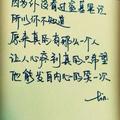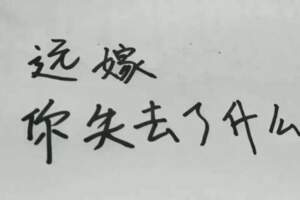那一年我還在上學,一日,母親和舅舅到礦上參加一個婚禮,晚上才能回來,讓父親給我做午飯。
中午我放學回來,家裡一股焦煳味,很濃很濃。
父親是要給我做燜米飯,西紅柿炒雞蛋。米飯燜在火上,準備炒雞蛋時,他怎麼也找不見蔥。蔥就在院外的一個箱子里放著,他不知道,就跑到菜市去買。菜市在哪,他也不知道。等他買回了蔥,火上的半鍋米飯燒焦了,下面的焦成炭,上面的也讓焦煙熏成黑紅色,不能吃了。
我進家時,他正在嘩嘩地洗鍋,鍋里是半鍋黑水。焦飯貼在鍋底,他用鏟子狠狠地鏟,可怎麼也鏟不起來,水濺得到處都是。
「俺娃回了,可爹把飯做煳了。你看這灰的、這灰的。」他很抱歉的樣子,忙忙亂亂地洗鍋,跟我做著檢討。
以往我一回家,飯就熟了,還可以跟同學們玩。今天有點不高興。
「就怨爹,就怨爹。」他繼續做著檢討。
「這多會兒才能吃飯?」我問。
「快當,快當。」他說。
「鍋還洗不起,多會兒才能做熟?」我說。
「不洗它了,不洗它了。咱們換個鍋。」他說著,把焦鍋端起,放在風箱上。
「我要誤課啦,走啦。」說著』走了。
「招娃,招娃,爹給俺娃下挂面、下挂面。招娃……」他追出了街門,沖我喊。
我理也沒理他,急急地走著,往學校去。
當時我是在大同五中念初二。
學校有規定,不許學生早到,上課的前半個小時才開校門。我來得早了,而且是太早了,少說也早來了一個半小時。我進不去學校。那是個秋季,但天很熱,我捧著臉坐在校門外的樹陰下,有隻貓過來了,看我。我沒理它,它看了一陣,覺出我討厭,轉身走了。
我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我後悔不該賭氣不吃飯。下挂面,是完全來得及的,當時我也清楚,可我就是為了想叫父親後悔。誰叫他沒把飯給我做好。
想起小時候,我們小孩子在院里耍,把毽子踢上了廟院的房頂,我從門樓爬上了牆,從牆頭又上了廟頂,去找毽子。聽著孩子們的吵鬧聲,我父親出來,一看我在那麼高的廟頂上,他嚇壞了,可又不敢罵我,只是說「小心、小心」,他那個著急呀,急得臉都變了色。我在上面往哪兒挪,他在下面也往哪兒挪,兩手平端著,護我,防著我萬一掉下來,他好接住。
他的那個急樣子,我永遠都忘不了。.可我不該用不吃飯來讓他心急,我真不該。孩子沒吃飯就走了,他現在不定急成什麼樣子。
正想著,聽到有人「招娃、招娃」喊我。
抬起頭一看,是父親。父親小跑著過來了,還抱著個籠布包包。
「吃哇,快吃哇。」他看看四處,沒有個台台這樣的地方,他就「嗵」地坐在我跟前,盤住腿給我當桌子,把籠布包包放在腿上,解開。裡面是搪瓷盆兒,盆里是熱騰騰的挂面,還有兩個荷包蛋。
我的鼻子一酸,眼淚「嘩」地湧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