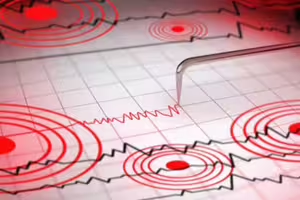我總是對他不滿意。認為他不夠愛我,而且,連句動聽的話都不會說。
他從來不說「我愛你」這三個字,即使愛得最熱烈的時候,他從來不叫我的名字,總是「哎,我說——」,「我說」就是我的名字了,下面就是他要說的事了。比如,他要一條毛褲穿;比如,他要一粒感冒藥,語言沒有任何感情溫度。
我曾暗暗發誓,下一輩子再找愛人,一定找個浪漫的多情的,一定找個叫我「親愛的」那種男人。
我在那天早晨大呼小叫,說自己又掉了好多頭髮,然後對著鏡子梳頭髮,一邊梳一邊問,「你說我是不是老了?我怎麼老掉頭髮呢?你看,我的眼角還有了魚尾紋。你看,我的皮膚還不如以前細膩了?」其實我想得到他否定的答案。這樣可以讓我不再這麼敏感這樣痛苦了。可他說:「可不是嗎,你以為你是妖精千年不老啊!你的頭髮是不如以前好了,搞對象的時候一大把,又黑又亮的!」
「這個該死的!」我罵著,怒髮衝冠地衝出來。然後說:「瞧你那老樣吧,一個老男人!」
他再不還嘴了,眼睛看著電視。
幾天之後,他買了好多黑豆來,我說你這是幹什麼?他說你熬粥吃吧,同事李大姐說長頭髮,越吃頭髮越多。
我心頭一陣熱,什麼也沒有說。
跟他商量去麗江旅遊的事,我說據說那是最小資最溫柔的一個浪漫寶地,我們去吧。他說那塊地方快被去爛了,有什麼去頭啊,咱倆得一萬塊錢,老家來信了,說咱家的老房子還要翻蓋呢。我聽了就氣,這個人太沒有情調了啊,我們一起旅遊的次數太少了,就是2000年的時候去了一次蘇州,還是跟他出差去的。他總是說旅遊是最沒有意思的事情,特別是跟著旅行社,簡直是一幫人去打狼,走走停停,吃飯上廁所拍照,沒什麼意義。這樣一說我也覺得索然,可是,他也太沒有情調了。
幾個月之後他說你準備準備吧,我說準備什麼啊。他說去麗江啊,有一個攝影隊,不是跟團,你又愛臭美,讓他們拍你去吧,我工作忙就不去了,全是我哥們,你放心吧。
我衝上去摟住他,他說,「別,別,你剛吃了大蒜吧,我受不了。」
最近胃總是不舒服,我天天嚷,總說,疼啊疼。他回過頭給我一句,「死不了。」我氣瘋了:「你怎麼知道我死不了?」他說:「要是真疼早就去看了,疼,嚷嚷就不疼了嗎?奇怪。」「你才奇怪,我說你知道關心人嗎?我死了就讓你打光棍!」
「可你死不了啊,我知道你死不了。」
我病不死也會讓他氣死。
我倒在床上委屈地哭。病了還盼望我死?有這樣的男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