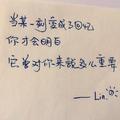3年前的一個冬天,我探望男友楠,來到海拔四千多米高度的雅魯藏布江邊。那裡有一個小哨所,就三個大兵,楠是班長。
我到達後的第3天,又一位客人來到了這個孤單哨所。客人是位漂亮姑娘,叫雪蓮,人和名字一樣美麗。雪蓮也是來探望男友的,江對面有一個空軍大峽谷氣象站,她男友阿兵是那裡的工程師。雪蓮在路上奔波了10天,才到達這個小哨所,但由於江面上結了一層不厚也不薄的寒冰,船不能劃,人也不能走,所以她只得先在這個哨所待下來。
當天下午,楠就拿起電話,接通了空軍氣象站,但那邊說阿兵已隨中科院考察隊進大峽谷考察了,過幾天才能回來。
就這樣,雪蓮在這個小哨所住下了,跟我搭一個鋪。楠說,當一個高原兵不容易,一個女孩子能夠千里迢迢不畏嚴寒來到這裡探親更不容易,讓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她。
第5天,江面上的冰依然不厚不薄。楠再次搖起電話機,扯著嗓子呼叫空軍氣象站。但是話筒里除了風聲外什麼也聽不見。我發現,雪蓮渴望的眼神在楠摔下聽筒的瞬間變得黯然了。楠覺察到她的反應,眉間也是一團黯然。
轉眼間,就到了第10天,電話里說阿兵還沒有回來,而江上的寒冰依然沒有變化。這天早晨剛剛起床,就聽雪蓮說:「我得走了,我請了30天假,在路上走了10天,在這個哨所等了10天,再不回去就超假了。」
我、楠跟那兩個哨兵都面面相覷。尤其是楠,看到雪蓮落寞的表情,好像不能見阿兵,是他的過錯,連聲對雪蓮說「對不起」。我勸雪蓮,10天都等了,還在乎這幾天?如果你前腳走後腳阿兵就回來了那多揪心!雪蓮沉默了,過一會兒說,可這冰還是那麼不厚不薄……
五個人一時沉默無語,雪蓮則焦急地來回踱著步子。忽然楠自言自語地說:「不行,我得請示一下,用炸藥把冰炸開!」他打了電話給團部,但又是兩天過去,團部一直沒有迴音。
這天,楠從團部回來,對雪蓮說:「炸冰的事兒,團部還在考慮;我到江邊去看了,還是不能行走,也不能划船,吃過飯後,你就收拾東西準備回去吧。」我聽了有些難過,為阿兵,為雪蓮的愛情。
那天我們沒有做飯,只是拿了些罐頭當早餐。楠端起杯子對雪蓮說,你就要走了,軍人不許喝酒,就讓我們以這杯雅魯藏布江的水代酒敬你三杯吧。一是祝你一路順風,二是希望你明年再來,三是請你講一講你和阿兵的故事。雪蓮就說:「好,我明年一定來。現在,我就講一講我和阿兵的故事吧。」
雪蓮說:「我們的故事其實很簡單,我和阿兵是中學同學,他也是我的第五個男朋友……你們不要吃驚,我們都是同學。前四個男友都比阿兵有錢,有地位,他們為我大把大把地花錢,從來都不吝嗇。金錢蒙住過我的眼睛,也擦亮了我的眼睛。當我對愛情一次次絕望的時候,我聽到一條消息,說阿兵大學畢業後,積極要求參軍並主動進了西藏。我就在電台為他點了一首歌:《青藏高原》。阿兵聽到這首歌后,主動聯繫我,然後我們就相愛了。從此,我把感情從泥潭裡撥了出來,給了軍人,給了西藏。現在,我認識了你們,我更堅信自己的選擇沒有錯。這次沒能見到阿兵,我很難過。離開你們,我心裡也很不好受。」
雪蓮見我們的神情有些酸楚,就說:「我給你們唱首歌吧。」然後,她便唱起了那首《青藏高原》。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遠處河對岸的喇叭里也傳出了《青藏高原》的優美旋律。雪蓮的眼睛裡立即閃出異樣的光芒,激動地說:「是他,一定是他!他說過他每次從外面回來,氣象站的戰友們都會為他播放這首歌。」說完,雪蓮忘情地衝出了哨所。
這時,電話鈴響起,團部的命令下來了:把冰炸開,送雪蓮過河。楠的臉上,現出少有的喜色。他拿起酒瓶,「咕咚咕咚」喝了幾口江水,抱著炸藥包就往江邊跑去。臨走,他對我說:「江上兇險,那兩個新兵又都沒有經驗,還是我這個老兵去吧。」
楠抱著炸藥包,往江里走去。就在炸藥起爆的那一瞬間,突然一陣狂風吹來,楠的身形晃了一晃,滑倒了……一聲巨響過後,等我從驚恐中反應過來,江面已是一片血紅……
楠死了,死在為這鐵血高原上一個大兵的愛情團圓中。追悼會那天,團部幾百名官兵全都來了,在小哨所的壩上,他們一齊向他默哀致敬。阿兵也來了,雪蓮緊緊地抓住他的手,滿眼淚痕地說:「我對班長承諾過,我明年還要來!不管明年你有沒有退伍,我明年都一定要來!」阿兵拚命地點頭。
「楠,明年我也會來。我會到高原來看你,這兒,是你的家,也永遠是我的家。」我沒有流淚。在那塊漆黑的墓碑上,刻著「楠之墓,愛妻秀敬立」八個血色大字。我的手中,就緊緊地攥著那張兩天前楠從團部領回的退伍證。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楠曾對我承諾,等回到家鄉的小城,我們就去領取結婚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