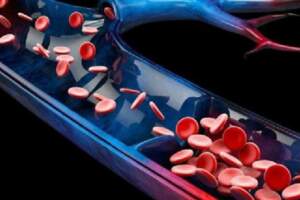只因為徐悲鴻和張道藩太大的知名度,她不期然地成為民國兩樁最醒目情事的女主角,但所有人都忽略了她也是民國時期一名職業女性——當過大學教師的一代才女……
她遇到徐悲鴻時,叫蔣棠珍,已是蘇州望族查家的準兒媳,可她當時偏偏18歲。18歲的女孩子,正是需要崇拜、愛慕某個人的時候,蔣棠珍也不例外,未婚夫沒有在她面前樹立起偉岸的身影,而另一個男子,卻具備了這種風範。
人生的十字路口,總會有一個重要的人,影響著你的一生。這個人,是我們道路上的槓桿,他或許只是無意做過,卻扭轉了我們人生的軌跡。徐悲鴻就是蔣棠珍生命中的那個人,自從遇到他,她的人生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文靜嫻淑的女子到能在一個深夜和徐悲鴻逃跑到日本的大膽女性。
兩人來到日本後蝸居在一家旅館裡,他不但給了她新的貧窮漂泊的生活,也給了她一個新的名字——碧薇。在日本的日子過得很清貧,但有愛情的滋潤,兩人也樂在其中。徐悲鴻到了日本,如醉如痴地喜歡上了日本的仿製原畫,見到喜歡的,就毫不猶豫地買下來。而他們身上,僅僅帶著2000元,儘管蔣碧薇不買衣服,不買鞋子,心甘情願和丈夫受苦,可還是不到半年,錢都花光了。
當時的徐悲鴻,雖有幾分才氣,可是美術造詣和名氣都還遠遠不夠,畫的畫根本沒人看。沒有經濟來源,只有回老家籌錢。當初出來的時候,蔣碧薇就沒有想到還能回去,現在丈夫窮困潦倒,她不得不回去求父母。兩位老人心疼女兒,也就接納了徐悲鴻。
不久,在康有為的幫助下,他們重新遠航,到法國繼續深造。她想,只要有了學費,自己可以做女工補貼家用。一個大戶小姐,淪落到做女工的地步,也是難為了她。
1919年3月,徐悲鴻和蔣碧薇順利到達巴黎。徐悲鴻進了法國最高國立藝術學校,蔣碧薇進了法語學校,先練習法語。但當時人生地不熟,語言也無法交流,一時很難融入當地的生活。那段時間,是兩人生活最為清苦的時期,但也是兩人感情最為融洽的時期。
她身材窈窕,氣質修養俱佳,21歲的女人最愛打扮,可是,蔣碧薇卻沒有條件打扮自己,為了看上的一件風衣,她路過那家商場無數次,可最終捨不得買,而是悄悄地把飯錢省下來,給他買了一塊懷錶。甚至有段時間兩人幾乎斷了糧,他抱著她,沒有吃飯,互相用體溫為對方取暖。她陪著他在巴黎度過了9年最艱苦的日子,挺過了生命里的嚴冬。
走的時候,徐悲鴻一文不名,蔣碧薇帶著私奔的罪名;回來的時候,徐悲鴻事業有成,蔣碧薇也是苦盡甘來。1927年12月,兒子出世,一家人其樂融融,後來兩人在南京買了房子,她專心在家撫養孩子,他辛苦去大學授課。孩子漸漸長大,她為了消除寂寞,就仿照法國的沙龍,舉辦了一些舞會,徐悲鴻回來的時候,並不喜歡這種娛樂形式,往往一回來就奔向畫室,漸漸和她疏遠了。
大凡藝術家,都有一顆敏感的、活躍的心靈。而這顆活躍的,時時處在騷動狀態下的心,正是藝術創作不可缺的源泉。在法國留學期間,徐悲鴻沒有錢請模特,蔣碧薇就是他的模特。回了國,徐悲鴻對蔣碧薇已經缺乏了戀愛時的感覺,此時,他需要一把火焰,重新燃起自己藝術的火種。這顆火種就是中央大學的旁聽生孫多慈。
知道此事後的蔣碧薇痛苦不堪,她一面安慰自己,徐悲鴻不是那樣的男人,一面又覺得徐悲鴻肯定是嫌自己老了,她在這種矛盾的愛情里掙扎。直到那天走進徐悲鴻在中央藝術系的畫室,當看到那幅《台城月夜》,憑著女性特有的直覺,她感到,家庭的大廈倒塌了。
她對徐悲鴻的愛,是愛,更是迷戀,不顧一切地投入自己的感情,殊不知這樣的投入本身就有不被全心呵護的危險存在。她的愛又那麼專制,她的性格令她的愛無法妥協於任何形式的不專一,於是她嫉妒、諷刺、控訴,而這些無休止的征服手段只能以感情的決裂為終止。他們為彼此造了一座地獄,儘管他們彼此相愛。因為相愛,所以錯不在他們本身,不在他們的行為,也不在他們易變的情緒,錯在他們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雖然最後在孫多慈父母的干涉下,兩人分手,她好像是勝利者,可是爭取到最後,她忽然發現:她錯了。經歷了這場婚姻保衛戰,她覺得自己不愛徐悲鴻了,自己原來並不了解這個男人。這男人,也從來沒有珍惜過自己,與其硬在一起痛苦,還不如愉快分開。
蔣碧薇是一個心氣極高、也很美麗的女人,假如不嫁給徐悲鴻的話,圍在她身邊的男人是不會少的,張道藩就是一例。
1924年的張道藩,和徐悲鴻一樣,也是一位學習繪畫的窮學生。徐悲鴻當時在畫界已經小有名氣,張道藩慕名前來拜訪。從那一天起,丘比特之箭就射中了張道藩的心臟。
1926年2月,張道藩終於鼓起勇氣,給蔣碧薇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長信,面對張道藩的表白,她採用了「冷處理」的方式。表白未果後,張道藩和法國姑娘素珊結了婚。
決心做一個妻子的理想破滅了,在茫茫的人海中她總該抓住一點什麼,這時,一雙援助的手向她伸來,這就是張道藩溫暖的手。
他們的感情始於抗戰的烽火。是他把他們孤兒寡母送上了逃難的船,又是他一次次去看望她,安撫她受到驚嚇的心,給她溫柔、體貼的關愛,給她物質的幫助和精神的鼓勵。他給她介紹工作,讓她挑起了生活的重擔,獨立地支撐著一個家。
抗戰8年是他們熱戀的8年,像所有熱戀中的戀人一樣,他們體驗了所有的快樂、等待、痛苦、折磨,寫下15萬字的情書。所以,1940年,徐悲鴻從新加坡回國,面對未來:選擇愛,選擇一個天才的畫家;還是選擇被愛,選擇做張道藩的情婦?在這艱難的選擇中,她選擇了情婦角色,因為她想要被愛的幸福。
抗戰結束後,她成了他秘密的情婦。1949年,兩人來到台灣,張道藩的妻子素珊與母親、姐姐和女兒去了澳大利亞,一走10年。蔣碧薇和張道藩公開同居了10年,她全心地照顧他的起居,雖然不是妻子,卻負起了一個妻子的責任。可是到了1958年,他對她說:「我到了澳大利亞以後,如果素珊她們提出想回台灣的要求,叫我用什麼理由拒絕她們呢?」軟弱的張道藩,20年前就說過,他一定會給她幸福,可是現在,當他們已經公開生活10年時,他卻向她提出這樣的問題。聰明、堅強的蔣碧薇無論如何也不會回答。她渴望與所愛的人一起生活,那是愛情最終的歸宿,她也渴望愛情走向婚姻,但她並不認為一定要用婚姻來堅守愛情,這時的她只能選擇離開。
與張道藩分手6年後,蔣碧微完成50余萬字的回憶錄,分為上下篇,上篇為《我與悲鴻》,下篇為《我與道藩》,在皇冠雜誌連載,轟動一時。兩岸隔絕,她暮年獨居近20年,孤獨離世。
她去世時,書房裡掛著張道藩為她作的肖像:她面容憔悴、神色慘淡,頭髮上還插著白花;卧室里則掛著徐悲鴻為她作的肖像《琴課》:臉部微斜、脈脈含情,專註地拉著提琴。兩幅畫中最相似的是眼睛:明亮深情。因為作為一個女人,無論愛與被愛,她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