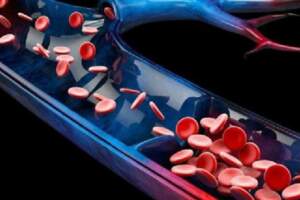9歲成名,文藝女青年、天才、學術女、中國年齡最小的期刊副主編……這些都是外界強行披在蔣方舟身上的條條披肩,與她的內心並不搭調。這個女子,倘若一定要用一個詞來形容的話,最貼切的,應該是清醒的誠實吧。
【保持清醒的成長,脫離軌道的勇氣】
在清華大學,蔣方舟不知道自己怎麼就被變成了一枚學術炮彈。她幾乎每天遭遇的情形都是這樣的:每每要小組展示成果,需要找一個發言人時,小組成員總是第一個想到她,展示之前,不忘叮囑:「待會兒發言的時候,你需要繼續說你擅長的那一套很嚇人的詞,把老師和觀眾都忽悠倒就可以了。」聽到這話,她有微微的心酸,覺得自己不再是個人,而是個沉甸甸的大殺傷力武器,被發射出去,俯衝進人群引起一陣暈頭轉向和不明就裡。最好笑的是,每次課或者講座結束,總有一個和她一樣裝了一大堆名詞和長句卻沒機會傾倒的學術達人找她「交流」。這種交流經常是雙方把一盆盆名人名言和巨大詞彙往對方身上砸去,就像打雪仗一樣。
有法律系的同學抱著討教的心態來求助蔣方舟。蔣方舟告訴了他秘籍:讀書,在每個以「主義」結尾的詞上重重地畫上圈,看到長長的外國人名就激動得熱血沸騰;只要是複雜的數學模型就趕緊抄在本子上;每每學會一堆新的術語名詞,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去炫耀;課堂或講座一宣布提問時間,就以將要把自己發射出去的姿勢舉手發言,滔滔不絕地講上十分鐘,然後酣暢得意地問:「請問您怎麼看?」這番速成果然很管用。當看到對方某次成為學術的中心論者時,蔣方舟卻冷汗直冒——「這種高級形容詞磚砌起我微薄的優越感,不讓人看出我一無所長;佶屈聱牙的長句嚴密地保護我,不讓人看出我的自我思考能力已經悄悄萎縮;一連串的作古哲學家掩護我,不讓人看出我只是一顆裝滿詞彙的炮彈。」
於是,她決心改變。還是一次課堂討論,坐在蔣方舟對面的人又開始源源不斷地向其拋射艱深語言,她沒有憤而反擊,平靜宣布:「請說人話。」這時,她只聽到自己撲哧一聲,輕盈地跳下高速運轉的學術流水線。
保持清醒的成長,就必須有脫離這個軌道的勇氣。即使軌道之外,並不許諾成功。陸續地,蔣方舟接觸了一些與眾不同的年輕人——有的高中時就放棄了名校,去讀企圖建造烏托邦的南方科技大學;有的大學生,刷海報,拉選票,參選人大代表;有的畢業了,也放棄名校、外企的職位,做一些他們認為能夠改造社會的事情——「因為所有的牆壁,其實都是門。」這是她的心得——如果一千個人中,有一百個人,有自己與大環境格格不入的內心世界;一百個人中,有十個人有離開這個跑道、忠於內心的勇氣;十個人中,只有一個人獲得了成功。那麼未來的社會,也許就會大不一樣吧。
【殘酷的誠實,令人產生生理抵觸】
蔣方舟寫的有關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篇文章,被認為是在那則轟動世界的新聞里最好的一篇。讀之,有著為其捏一把汗的凜冽。「作家有權利保持自己的遺世獨立,同時,他也必須和所生活的時代有某種同頻的互動……作家沒有改造社會的義務——他們絕大多數時候也沒有那種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誠實反抗社會的義務,有以正直對時代保持悲觀的距離的責任。對於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換代的革命,他更應該關心的是那些革命改變不了的永恆的人類苦難。」
每當重讀這段文字,還是忍不住再計算一下蔣方舟的出生年份。生於1989年,大家更願意把她說得再小一些,冠之以90後。可是,每當讀及這段文字,就會質疑她的年紀。是的,她的確是個天才,她也承認,自己是一個誠實得幾近殘酷的天才。
在她的書《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里,對於父親、母親、祖父母的情感描述得過於粗暴、灰暗和不留情面,以致很多讀者出離憤怒,甚至有生理上的抵觸。
對於這種反應,蔣方舟是得意的。她說面對白紙,她無法迴避,也拒絕美化童年。她深知哪怕再熟悉的旁人,也只不過讓你失望憤怒,而家人、爹媽,畏懼、溝通之困難,有時是真的可以讓你絕望得心裡落了一層又一層灰,說不出來的苦澀。而她,只不過把這種苦澀原汁原味地端了出來。這種殘酷的描寫不是她不愛父母,只是用文字這個特長貢獻了個人的經歷。其實,親情里所有的和解與溫情脈脈都來得相當緩慢,而且經常是以死亡為臨界點的。這也是她坐在電影院里看《歸來》時,怎麼也無法按照張藝謀埋下的淚點,有節奏地落淚的原因。倒是當她在書中寫道:「父親有一天來到北京,忽然,覺得這位籠罩在我童年的龐然大物在首都顯得小了,弱了……」這樣的念頭,才是一個孩子對父母的真念頭,才是親情無須矯飾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