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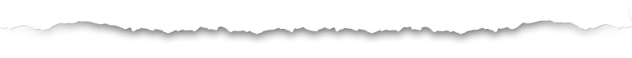
相愛是兩個獨立的人並肩前行,而不是我的世界只有你,喜怒哀樂都系在對方身上,在另一方成長的時候,你也要一起邁開步子。否則,你倆只能做愛,不能相愛。
連續好幾天了,林子一直處於「末日將至,人之將死」的狀態中。她躺在北京的四環外的某個地下室里,看著混沌的夜色,一直在思考,愛是什麼,生命有何意義。
林子並不是文藝女青年,她之所以忽然變得如此「矯情」,只因為她太痛苦了。引發這種連綿不盡的痛苦的,是她的男友王小偉。就在上周,他忽然說:「分手吧!」然後搬離出租屋,徹底消失。
王小偉也是北漂族。來自四川的一個小鎮,170的身高,長相不出眾,搞IT,是那种放到人海就消失不見的人。在他身上,林子看不到逆襲的希望,也無法期待天降橫財的奇迹。
但是,她需要一個人,和她在冷漠而浩大的北京互相取暖,於是,在某一個冬天,他們靠攏並相愛。
三個月以後,林子退了自己的房子,搬去和王小偉同住,一來節省房租開銷,二來可以更靠近對方,尋找身心的慰藉。
兩個年輕人,荷爾蒙爆棚,對彼此的身體自然無比迷戀。他們根本無暇思考為什麼要在一起,就已經滾到了一起。
樓板薄,鄰居隔牆有耳,就把被子鋪到地上。有時天冷,暖氣又燒得若有若無,但功課照做。
因為做愛頻繁,時常裸露,兩個人輪著感冒,可是,愛也像發燒的身體一樣,令他們熱氣騰騰,昏頭昏腦,不辨西東。

這時候的他們,就像兩個孩子,各自端著一盆火,邀請對方來自己的火上烤烤手,烘烘身子,暖暖心。一邊烤,一邊笑,整個北京城變成溫暖的火爐,令他們感到莫可名狀的舒心。
如果相愛的兩個人,都像開始時他們一樣,都在給予,都在表達,忘了索取,該有多好!可惜,愛,必然是有索取的。
兩周以後,他們忽然爆發爭吵。原因是王小偉到了12點多才回出租屋,而當天沒有加班,也沒有應酬,林子打了60多個電話,他一個沒接。
她感到異常的焦慮,二話不說,收拾好東西就去了閨蜜家。連續三天,都沒有開機。王小偉在第三天下午,在林子公司樓下等了2小時,才等到了她。
她置之不理,他亦步亦趨;她冷若冰霜,他好顏好色;
她回手甩了他一巴掌,他愣了一下,然後告訴她:「前天晚上我在公司睡著了,我太累了……」她不信,他再解釋。
三小時后,他們終於和好。像往常一樣,坐著地鐵,又轉了一趟公車,回到出租屋。做飯,做愛,一切都和平時沒什麼不同。
但是,林子對愛的不安、匱乏、緊張,開始撕開口子,讓王小偉看到了裡面黑洞洞的恐懼。王小偉對這種恐慌非常熟悉,因為,他也是這樣的人,像一個乞丐一樣希望獲得他人源源不斷的關注和愛。
是誰說,世界上所有的行為只有兩個目的:表達愛,索取愛。無論你或你身邊的人在做什麼說什麼,看起來多麼的過分,多麼不可理喻,歸其根本,這裡面的動機:不是在給予愛,就是在索取愛。
林子和王小偉之前的熱情似火,互相體諒、支持、理解、纏綿,就是在給予。當一方給予,另一方也會給予。當一方的愛給得如此闊綽,另一方也不會吝嗇。這樣,愛就會能量流動,積極循環,令兩人都深感愛意盎然。
但是,當愛進入互相索取,「我要你關注我,我要你哄著我,我要你每時每刻都想到我,我要你滿足我……」另一方在這種逼迫下,本能地覺得累,覺得身體被掏空,於是也想索取。
如此一來,關係就進入惡性循環,我要,你也要;我要更多,你也想要更多。周而復始,不斷輪迴,於是痛苦。
愛令人痛苦,不是一方大奸大惡,另一方至善至美,而是因為以下兩點原因:你要,他不給;他要,你不給。
究根結底,我們都是缺愛的人,每個人都像乾渴的沙漠一樣,期待別人給予清水,給予雨露。
問題是,當沙漠遇見沙漠,都想汲取,都想要,就會導致一個結局:兩個人都變得更加乾旱,更加饑渴。
這種饑渴是一晚上做3次愛都無法滿足的匱乏,也是一天說100句情話也無法修復的缺陷,它來自生命深處的恐懼。就像靈魂里安了一個不斷工作的抽水泵,需要向外不斷地抽取愛、能量,以填滿空洞的自我。
王小偉是這樣,林子也是這樣。

他們的互動漸漸進入一個僵局:你怎麼老是想著你自己。你為什麼不關注我啊,你為什麼不哄著我啊,你為什麼不滿足我啊?那你呢?你又為什麼不關注我?不滿足我?我也想要啊,你怎麼不給我啊?
互相折磨,互相控制,惡性循環。
這種輪迴一定要等到有人開始覺察,開始成長,站起身來,變成一個真正的大人,才會宣告終止,王小偉是先成長起來的那個人。
他開始承擔責任。物質的,精神的。他接更多的活,升到更高的職位,寫更長時間的代碼,更專註於專業技能的提高。
同時從原生家庭開始,自我診斷,自我療愈,以更好的狀態與戀人相處。可是,幾個月以後,他發覺自己累不堪言。
林子依然不安。他晚歸,她焦慮;他獨處,她緊張;他微信上有漂亮異性,她擔心;他沒有及時回話,她歇斯底里。
面對林子強烈的不安全感與控制欲,王小偉開始有意無意地逃離。而他的逃離又導致林子更旺盛的不安,對他的控制越來越緊。
比如,她當面鑼,背面鼓地希望他能向她求婚,希望他能在今年年底能存上30萬,希望他父母和她父母一起出資,在北京買個小房子,希望可以不用擠地鐵上下班,希望王小偉能更強大些、成功些、牛逼些,給她一個安穩清閑的生活。
而在感情方面,她的控制也在加強,比如,她要他每天8點以前回到家,如果沒有,電話一個接一個地打,直到他出現在她面前。
有一回,王小偉和朋友們在唱K,林子在出租屋裡,感到一種若有若無又無法擺脫的不安,她給王小偉電話,結果,因為包房太吵,他沒聽到。
不安就變成了焦慮,她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打。依然沒接。焦慮就變成了惡意的猜想,猜想就變成了恐懼。
她無法自制地,給王小偉的每個朋友打電話,一邊打,一邊又對自己的表現深感不安:我這樣好像太不大氣了!這樣一來,這種自我貶低又加重了她的不安。
她就在這種折磨中,精神緊張得不行,等到王小偉回家,一進門,她大哭出聲,登時崩潰,大喊大叫,歇斯底里,憤怒得猶如受傷的野獸。

王小偉被嚇到了,他能理解她的委屈,卻無法消化她的瘋狂。他覺得:「你他媽的是不是有病?不就幾個電話沒接到,你至於嘛!」
可是,之於林子而言,她卻被恐懼所控,對王小偉、對未來、對他人,都緊張不已。她擔心被別人笑話!她焦慮於男友的若即若離,冷若冰霜!她恐懼生活空空如也,自己什麼也抓不住。
於是,在王小偉看來很尋常的小事,可能都會刺激到她。她需要王小偉靠近她,擁抱他,把她抱到床上,狠狠地要她,吻他,填滿她,然後告訴她:
「一切都會好的,相信我!」
「我那麼愛你,怎麼可能會離開,你別傻啦!」
「別人都覺得你又漂亮又能幹,怎麼可能笑話你,大家羨慕都來不及呢……」
她需要王小偉更強大,更出色,更靠譜,更滴水不漏地保護她,更無懈可擊地工作;她無法贏得天下,無法錦衣玉食,無法成為人上人,無法在北京城立住腳跟,於是,她希望王小偉能為她做到,如果他做到,她就安了心;
而這些心思,她都不能讓王小偉知道。她不能讓他知道自己的自卑與無能,也不想讓他看到自己的敏感與脆弱。她覺得羞恥,她不願意裸露真實的自己。
於是,她用指責來轉移自己的恐懼,用攻擊來掩飾自己的軟弱。當她揮舞起語言的兵刃,滿臉殺伐,語氣兇狠,她會暫時擺脫虛弱,看起來強大無比。
心理學家早已說過:攻擊是一種憤怒的能量。憤怒是一種次生情緒,為了掩飾內心深層的創傷。比如,尷尬,無力感,委屈,慌張,焦慮等感受,我們都不喜歡,也不想面對,更不願意表達,就會把這個情緒演變成憤怒釋放出來。
只是,林子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真正令她受傷的,不是王小偉,而是她自己。她的自我價值感太低,力量不足,恐懼太濃。
當她無法自我覺察,自我成長,那麼,這就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令她不得安寧。

和誰上床,都會在激情褪卻時,發現這些病症又冒出頭來,發出信息:「我疼,我怕,我要……」和誰相愛,都會在甜言蜜語巫山雲雨後,看見它的臨床反應。
和誰結婚,都會在日常生活里,發現它已成為你常客,不請自來,揮之不去,令你無可奈何。
林子卻無法真正自省,她一直以為,這是女人正常的反應。於是,不反思,也不積極溝通,只是辯解,或在衝突發生后,一味評價與指責對方。
可是,王小偉越來越無法適應她的索取,他在內心哀嘆:林子,我不僅想和你做愛,我還想和你相愛啊!
可是,相愛不是兒戲。相愛是有條件的,它要求相愛的對象,是兩個健全、能成長、能自我負責的大人。
只有兩個大人,才能互相支持、理解、體諒、欣賞;一個孩子和一個大人,只能照顧與被照顧,依賴與被依賴,討好與被討好,抱怨與被抱怨。
一個孩子和一個孩子呢,則在歡喜時做愛,愉快時纏綿,不爽時指責,受傷時攻擊,無法處理衝突時則向外界控訴,讓「各位父老鄉親都來評評理」,這樣的愛,當然不能成為彼此的成長液。
愛不只是做愛,愛是兩個人精神上的共同成長,是真正的互相看見與接納,是共同承受命運,一起創造親密。
如果不能,那就友好分手,放對方一條生路。
王小偉終於在2017年3月的某個夜晚,向曾經同床共枕如膠似漆的戀人說:「分手吧!對不起!」那一刻,林子感覺世界像被人摁了暫停鍵,無聲無息,動彈不得。
她怔在原地,忘了哭,也忘了叫,只覺得整個人都在下墜,下墜,往無底的深淵下墜。
而在下沉的間隙里,她看見黑色的深淵中央,蹲著一個小小的孩子,她睜著驚恐的圓眼睛,對她說:「我要長大,我要真正的愛!」
愛不是捆綁,而是滋養。愛不是吞噬,而是自由。愛不是依賴、指責與抱怨,而是接納、承擔與負責。
愛不是體液的交換,荷爾蒙的灼燒,而是理智的清明,能量的飽滿,精神上的肝膽相照,生活上的同甘共苦。
懂得了這些,愛就不會成為一次接一次的傷害,而是一場接一場的福蔭。
祝所有人都能通過相愛,尋到真正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