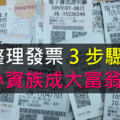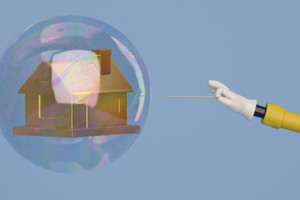「那真不是人幹的!」
在街頭五年,透徹大哥細數曾經做過的工作:舉牌、陣頭、派發DM等等。其中舉牌是持續最久的,但回憶起來,他卻屢次如此大罵。有段時間,常會有派報社聯絡人到台北車站地下街去找街友幫忙舉牌,透徹大哥就是這樣找到這份相對「穩定」的工作。
他們每逢六、日工作八小時,每小時可小歇十分鐘,午休一小時,日領800元,平日則為750元。透徹大哥年事已高,膽、胃都相繼動過刀,無法勝任日薪1,200元的粗工,工作選擇、收入來源相對少的他,一個月僅有6,400元入帳,在台北不只無法掙得安身之所,連吃、穿等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
「做了舉牌,我才知道什麼叫風吹日曬雨淋。」
原來,舉牌人不是隨意地站在一旁扶著廣告牌即可,還必須把牌子拿得端正。有些牌子為了吸睛做得十分巨大,在一些風大的十字路口,一個拿不穩就會壓到舉牌人。
天熱要披著公司的外套,雨天只能穿雨衣,這就是舉牌人的生活。這些年來,透徹大哥舉遍天母、陽明山上豪宅的廣告牌,卻只能在停車場度過自己的四季。
平日裡,大哥也會接一些陣頭的工作,日薪500到800元不等。他還曾被找去為抗議活動充人數,「好像是靠近台北車站關於媒體的一個抗議事件吧,那場拿了400塊。」乍聽之下,價位竟比起其他工作低了不少。「臨時工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有時也不知道對方會給多少。」透徹大哥無奈道。
「啊對,千萬不要去發傳單!那個在大馬路上那麼多車,要趁紅燈的時候下去發給車主,綠燈前又要跑回來,又累、又危險!」 選擇不多,但工作經驗豐富的他,說到這些總能有分享不完的甘苦談。
這天下著大雨,我們跟著大哥走過西園路二段迂迴曲折的小巷,爬上陳舊卻別有風味的老舊社區。抵達他的租屋處後,我問大哥需不需要脫鞋?大哥說隨我們意,抬頭一看—竟是一整片雪白發亮的磁磚地板。
原來,自去年摔斷腿後無法繼續舉牌,透徹大哥就在社會局的協助下結束了露宿街頭的日子。現在的他,每天早上7點到10點會在附近社區打掃,以工代賑,結束後還會回家拖地。待一切都清掃完畢,他就拿著每日500元的工資,到附近超市買食材自行下廚,也分享給收入不多的室友們。
透徹大哥愛玩今彩539,小賭怡情,還研發出自己的一套預測理論,閒來無事就窩在房裡研究,或搭公車去附近的圖書館看報。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一年多。
透徹大哥是台南人,曾為空軍軍官15年,育有一對兒女。身體不好的他提前退役動手術,後來發現太太外遇而離婚。賦閒在家後,他開始賭博。一開始六合彩中了6、70萬,初嘗甜頭。接著十賭九輸,債務越陷越深,每個月累積2、3萬的卡債。最後,只得用老家房子貸了100萬來還朋友錢,並因為無法再負擔銀行貸款而宣布破產。
當時,透徹大哥只要再5年即可月領5萬,享受悠哉的退休生活。人生風雲驟變,透徹大哥只得在58歲那年北上求生存。年邁的他,在台北找不到工作,於是開始流浪過生活。
「一開始到台北齁,人海茫茫,也要衡量自己接下來的吃住,不能馬上去租旅館啊。」透徹大哥發現當時的台北車站地下停車場內,許多街友鋪了紙板就地入眠,就也加入他們一行。「不可能一開始就習慣啦,一開始怎麼睡得著,沒想到這一睡就是5年。」
夏天的時候,透徹大哥喜歡從台北車站步行到中山市場附近的圖書館休息,避暑之餘也看看書報,「更新一下社會資訊、進修自己」。來台北幾個月後,他的盤纏近乎用盡,在往圖書館的路上,瞥見公共電話亭上貼著恩友與救世軍的傳單,寫著教會免費供餐、盥洗的資訊。不久,又無意中發現車站後方的普濟寺每月有4天會發放素便當。就這樣,透徹大哥在最艱難的日子裡撐了下去。
如今,透徹大哥已經滿65歲,具備申請低收入戶的資格,可領將近2萬元的補助金。但他告訴我們,只要還有能力靠自己,就不會去申請;還特別強調,早在工作穩定後,他就不曾到恩友吃飯,只去救世軍洗澡,時間碰上的話才拿一份便當。談起過往,透徹大哥總會帶著一些歉疚:「我不想成為社會負擔啦。」
曾經因為賭博而墜落的他,現在可以養活自己、可以供曾經一起流浪的室友一頓溫飽。雖然以工代賑的微薄收入,偶爾也會讓他入不敷出—房租、吃穿、看病複診及通勤費……然而,在這些生活瑣事之外,他仍然堅持著小小的嗜好:今彩539。
人畢竟不可能只是活著的呐,哪個人沒有一點癮、哪門興趣不花錢呢。
採光良好的房間裡,書桌上散放著一張張全開大小的539牌機號碼表。過著半退休生活的透徹,閒來無事就坐在那裡,用紅色簽字筆,一格一格地推算開彩邏輯、找尋本期的幸運數字,彷彿想要討回那些失落的過去。久了,竟也讓他研發出自己的一套理論。
「如果我贏了800萬,我一定要把一半捐出去!」
他總是如此嚷著。
延伸議題:關於工作,我想說的其實是…
早上8、9點,對許多人來說,正是通勤趕車,準備邁向一天開始的尖峰時刻。
等紅燈時,你從擁擠不堪的車潮中探出頭喘口氣,目光正對到了蜷縮在路邊長椅上呼呼大睡的身影。
身旁乘客發出「嘖」一聲,媽媽路過時拉緊了孩子的手。一切彷彿順理成章,你甚至可以猜測到九成精準的對白:「大清早不努力工作,難怪會變街友!」、「你以後要好好用功,不然長大會跟他一樣。」
在眾人庸庸碌碌的時刻仍未起身—「放棄抵抗、怠惰成性」,無家者被污名化的理由,看似切合著那些陪同我們成長的童話寓言:不努力者理當被淘汰;於是我們轉身,並未多想,繼續在生活中打拚,和那看似與自己毫無關聯的人生擦肩而過。
街頭打盹的身影,猶如冰山微微露出的一小角。當人潛入水面下,才驚訝發覺那龐大而悲傷的故事始末。
《遊民問題調查》中指出,高達7成以上的無家者有工作,但收入極不穩定,平均月收入不到6千元。此數據一出,便使大眾感到錯愕:如果大多數人有工作,為何仍時常可見大白天睡在路邊的身影?而一個月不到6千元的工作又是什麼內容?
為了記錄城市生存者常從事的工作內容,並親身體會其中感受,我們報名參加了非營利組織舉辦,為期三天兩夜的流浪生活體驗營。
露宿的第二天,清晨6點天尚未全亮,便被導師芫荽催促來到指定地點,此時已有幾位大哥大姐聚集—人們看起來侷促不安,彎著腰向點工的老先生打招呼。
開始算人頭時,我們卻突然被告知:今日點工人數已滿。
就在這瞬間,一天彷若被宣告結束。儘管我們不願放棄地四處詢問職缺,卻發現每種臨時工都是在前一天或早上7點時便已決定人選。天才亮,我們認知自己「好手好腳」,仍注定什麼也做不成。
「這就是街友禮拜一到四的常態:幾乎找不到工作。」導師說得平淡,我不服輸,想透過撿回收的方式,讓自己至少付出勞動、有份「踏實工作」。芫荽聽到卻搖搖頭:「你們自己去吧,我要補眠了。」最後,好不容易與流浪夥伴蒐集滿整車的紙箱,推到資源站一秤:68塊。
這是兩人半日勞動後的所得,不禁使人想起《泰利的街角》書中所描述的場景:一輛卡車駛入黑人貧困社區,吆喝著男性來從事粗工,卻沒人願意上車。司機咒罵這群人好吃懶做、只顧及時行樂。然而至今才明瞭,這群人並非目光短淺—反倒是早已透徹了解眼前的工作酬勞與辛苦不成正比,只有滿滿的勞累與未知傷害等在前方。
看著被叫起後睡眼惺忪的芫荽,正是因為體驗營有期限,使我們用盡全力與現狀搏鬥;而這街上的生存老手,則是來回了多少次徒勞無功後,終於決定放棄抵抗,用睡覺、發呆麻痺空胃,麻痺感受。
然後,長期背負著臭名的熟睡身影在此時恰巧被路人目擊,從此成為了「街友之所以是魯蛇」強而有力的鐵證。
絕大多數的無家者礙於學歷、經歷等外在條件不夠亮麗,僅存的就業選擇多屬於高勞力、高風險的非典型勞動,例如在工地揮汗如雨的臨時粗工,以及與房產廣告合為一體的舉牌人。這些工作時有時無,而當投入後,才發現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花在等待:等待被點名上工、等待通勤、等待下工、等待通勤返回歸處、等待一日的結束。
有人問,怎麼不去找份「正當」的工作呢?
然而,幾乎大多數的無家者們,都曾經有份「正正當當」、「腳踏實地」的工作。不少人自年輕起便在傳統產業中擔任學徒—塑膠、製造、成衣。卻在產業遷移至勞力更便宜的國家時,人與技藝一同被遺落在這片土地。
自工業革命後,時至今日普世仍信仰著機械解放人力,你我將能適性發展、追尋更多生命的價值;但事實卻似乎偏離了理想的藍圖,機器取代人的當下,其所帶來的「效率、產量」也同時成為了指標,以片面、抽離的角度衡量人的價值。單用生產力看待勞動者,便輕易合理化了對年邁者、身心不便者和落魄者的淘汰與切割。
街上的人們,曾經是握有一把釣竿的。如今卻得無奈地徘徊街角,無處伸張。
那麼,當下在街頭的工作,有辦法找到新的翻轉契機嗎?
從2015年開始進行「人生柑仔店」計畫,我們驚豔地發現街頭—這個平時被行人視為轉場的背景,街賣者們卻在此累積起了豐厚的經驗和社群:看似臨時性的工作,其實必須與周圍的店家、居民、消費者、同行乃至執法人員間,擁有一定的情感或默契,才能在人潮往來的路口安心進駐,不被取締或檢舉。柑仔店計畫中熟識的幾位頭家,帶領著我們看到街賣融入在地,與鄰居、店家、顧客成為了好友。
「這一行談的不只是賺多少,還有人際互動所帶來的成長與感動。有時候,一天賣不出多少,但只要有人上來問、有互動,就會想持續做下去。」過去一直支持著我們的頭家「校長」,即便冒著沒有生意的風險,他仍堅持不強迫推銷,「我把對鮮花做的研究,分享給顧客,讓顧客知道各種花該怎麼保存、可以放多久;我也會聽到顧客講自己種花、買花的經驗。這樣的教學相長,我覺得非常高興。」
「我需要工作,純粹就是希望自己持續工作。」一位街上的長者輕聲感慨。反思工作存在的意義,或許並不只為了追求肚皮溫飽、名利,或甚至主流認定的成功樣貌—工作,可能就單純地,是份注入內心的踏實。感受前進與累積,每晚閉眼前,會為明日將至而感到期待。
若人們需要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那一份提供尊嚴與安全感的工作,就理當為人所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