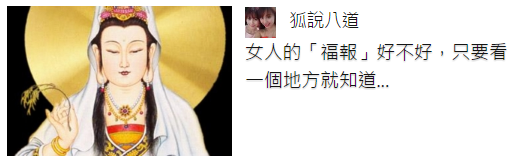陰曆每個月份的初一,我必去一趟響山寺,進香,拜佛。我曾經是個生意人,那些年月,利潤就是我頭頂上的神明。有了一定的積蓄後,我開始厭倦那種打拚的生活,終至退出了生意場。現在,我弄了點正經事,穩穩當當地做著。又因為經常來寺廟的緣故,每時每刻都感到心里很踏實。
響山寺的前面是一條小河溝,一座小石橋正對著寺的山門。幾年前,當我第一次來寺里進香時,就見到了黑瘸子。黑瘸子的一張臉黑得似鍋底,一條腿又細得像根鍬杆,而且還短了一截子,他的年齡和我相仿,都是四十多歲。
他坐在小石橋的欄杆上,一邊放著乞討的小鐵桶,另一邊斜放著他那隻油黑鋥亮的破拐。那條細腿的褲管總是卷起老高,冷天也是如此,以便最大限度地展示他那用以乞討的資本。他雖以乞討為生,但他的表情並不讓人覺得可憐,盡管如此,每次我都會往他的小鐵桶里放一點錢,少則幾塊,多則一二十塊。在我放下錢時,他會一連聲說幾個謝謝,那時我的心里就感到很受用,甚至會一下子冒出一個善良的“本我”,於是,身心輕鬆起來,感覺出了人生美好的滋味。
時間一久,彼此都熟了。有時,我還和他開開玩笑,問道:“兄弟!這些天買賣怎麼樣?”
他說:“不怎麼樣哩。祝你發大財啊!”
那次我去寺里進香時,沒有見到他。不知怎麼,心里竟感到失落,好像我必須施舍出去一點兒錢才能獲得心靈上的安慰似的。
再次去進香時,又沒見到他。因事耽擱,我來寺廟時已近中午了,從寺廟出來後,我就驅車直奔不遠處的一個農家酒館。我曾來這吃過飯,這里燉的小笨雞非常可口。
酒館的生意特別好,我進來時,竟沒有空座了。正當我要找服務員時,傳來一個喊“老板”的聲音。循聲望去,竟是黑瘸子。他正別別扭扭地半站起身,向我招手呢。我遲疑了一下,還是走了過去。桌子上已喝空好幾瓶啤酒,盆里的那隻小笨雞也沒剩多少了。和他對飲的是一個蓄著黑白相間胡子的半大老頭兒。老頭兒一雙刀片似的眼上下打量我。黑瘸子非常誠懇地邀我坐下喝一杯。本來,一見到他時我心里就有點不痛快了,現在,看著空酒瓶和盆里的燉雞,一把無名火在心底亂竄起來。一個靠乞討為生的殘疾人,竟如此又吃又喝的,這也太不像話了。
“兄弟!別喝多了,耽誤了你蹲橋頭。”說完這句話,我扭頭就離開了。
“那,慢走啊!祝你發大財。”大概黑瘸子也沒想到會是這樣一個結果。
回來的路上,我的心里還在憤憤不平。可我究竟不平在哪里呢?我絕對不是心疼我施舍的那幾個錢讓黑瘸子給禍害了,細細一想,我得承認,我是失去了憐憫的對象。我不能再想下去了,用口哨吹起了《高山流水》的曲子。
時隔半個來月後,我去山背面的觀音閣。順便說一句,凡是有寺廟的地方,我從來不吝嗇幾柱香錢。正當我埋頭爬山時,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喊道:“老板,發財啊!”
抬頭一看,黑瘸子坐在馬紮上,正朝我笑呢。他還怪模怪樣地留了小胡子。我頓時明白了,黑瘸子改行了,現在是算命先生。他的前面用四塊小石子壓著一張紙,紙上畫著八卦圖案,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
“喲嗬!你變得蠻快啊。”我揶揄道。
“嗨,沒辦法,得想招不是,光靠蹲橋頭已經過不下去了。上次在飯店你遇見的,那是我請的師傅。”他的話,也有自嘲的意味。
我下意識地摸了摸兜,立刻抽回手,兩手搓了搓。他這種身份,我不便直接給他錢,又不可能找他算上一卦。“這,買賣還行吧?”我問一句。
“湊合著吧,總比蹲橋頭強。”他笑道。
我半認真半嘲弄地說:“要不,你給我來一卦?”
他擺擺手。“你逗呐,”不過還是在我臉上注視了須臾,“還用說,大富大貴的命!”
“對啊,你就這麼說,誰不樂顛顛地掏腰包!”
黑瘸子再次認真地打量了我小一會兒,笑道:“我都不蹲橋頭了,可你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山上跑哩。”
我覺得他這話的意思是在笑話我白糟蹋了上香的錢。“這是在做善事。”我說。
“其實,你這也是在乞討。這里。”黑瘸子說著,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我怔在那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