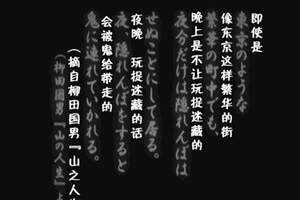對方發來的這條消息很讓我震驚,我甚至情不自禁的就轉頭朝窗戶外面看去,腦子裡第一個反應,就是有人在暗中偷窺我。
不過眼睛在窗外掃視了一下,這個第一反應就隨之消失了。就算有人偷窺到我半夜不睡覺,也絕對不可能推測出我是因為害怕做噩夢才不睡覺。
這個叫赫連的人,頓時就籠罩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他是什麼人?他怎麼會知道我的苦衷和無奈?
我產生了警惕,在我看來,我做噩夢,完全是因為那個大頭怪嬰的原因,所有和這件事有關聯的人,都在懷疑之列。尤其是赫連這樣來歷不明,突然就出現的人,更無法讓我信任。但他既然找到我,而且直言不諱的說出了那個夢,這就說明,他至少也是一個知情者。
「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的事?」我一邊用微信跟對方溝通,一邊就聚精會神的觀察著窗外門外的動靜,我居住的北環是整個陽城最荒僻的一段,入夜之後萬籟俱靜,我察覺不出有什麼異常。
對方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回應:「來吧,就差你一個了。」
赫連把我拉進了一個微信群,這個群的名字叫「夢源」。
這個微信群連同創建者加上剛入群的我,一共也只有七個人。現在是凌晨兩點半,正常人早就睡的昏天黑地了,可我剛被拉進去,群里就沸騰起來,有人一條一條的發著信息。這時候,赫連給我發來了私聊。
「你肯定在懷疑,懷疑我為什麼會知道你因為怕做噩夢而紊亂生物鐘。」赫連打字的速度不快,但每一句話都很清楚,讓我可以第一時間完全理解:「這個群里每一個人都和你一樣,快被那個噩夢逼瘋了。」
「噩夢?什麼樣的噩夢?」我的震驚更深了一層。
「一個頭顱很大的怪嬰,一片黑色的竹林,一個老村,還有很多穿着紅衣服上吊的人。」赫連繼續發來消息:「你,我,還有群里其他幾個人,都在做這樣的夢。」
我的大腦就和短路了一樣,甚至暫時失去了思維功能。事情的怪異和離奇已經完全超乎了我的想像,我自己一連幾天做同樣一個夢,這現象本來就讓人不能理解,可是讓我意想不到的是,不僅僅是我,原來還有其他一些人,也在被噩夢困擾著。
我把赫連發來的消息看的非常非常仔細,僅就噩夢來說,他絕對是一個知情者,因為他所描述的夢境,和我做的噩夢一模一樣。
「是,我是做過這樣的噩夢。」我沒有否認,我想知道更多的事,就必須跟赫連建立一種可以信任和溝通的關係,必須跟他交流,所以我心裏保持警惕,卻不能不說實話,我承認了噩夢的困擾,然後問他:「我很好奇,你怎麼會知道我在做這個噩夢?」
「是群主傳達給我的。」
這個群的創建者的ID叫影子,赫連不認識他。如果放到正常情況下,赫連估計也不會相信一個微信上的陌生人,但這個影子當時找到他的時候,直言不諱的說出了赫連的夢境,然後陸續提供了一份名單,赫連就按這個名單,把幾個人先後拉進了微信群。
我認真的瀏覽了一下微信群幾個成員的信息,微信群的成員列表,是按進群時間先後而排序的,影子創建了群,第一個拉進了赫連,然後依次是白領,隔壁老王,高富帥,丁靈,還有我。
在建群之後,群主影子就沒有再露過面,因為是微信聯繫,群成員都不知道影子在現實中的聯繫方式。
做噩夢的,一共有六個人,其中白領和丁靈是女性。
如果沒有這些信息,我可能不會多想,但一個城市裡,幾個不同身份,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突然就開始做着同樣一個噩夢,這種情況已經完全排斥了巧合的可能。
赫連,白領,隔壁老王,高富帥,丁靈,方懷……
這看似很普通的排列順序,一下子讓我捕捉到一個關鍵的要素。
我推測,只有親眼目睹了大頭怪嬰的人,才有可能做那個噩夢。焚燒大頭怪嬰的那晚,我趕到場裡的時候看到了一輛第一人民醫院的車,當時沒有考慮太多,但現在認真的思考一下,就會隱約判斷出,那個大頭怪嬰可能是剛剛出生,在醫院裏死去,然後拉到了火葬場。
這是一條看不見的鏈,群里成員的排列順序,其實就是親眼目睹大頭怪嬰的先後順序,赫連第一個目睹,然後是白領,隔壁老王……火葬場是最後一站,所以,我才會變成最後一個做噩夢的人。綜上,也就可以判斷出,赫連當時就在醫院裏,離大頭怪嬰最近。
我是這樣推測的,估計有一定的道理,不過轉念再想想,從醫院到火葬場,目睹過大頭怪嬰的肯定不止這六個人。其餘的人為什麼沒做噩夢?
「你是個醫生?」我私聊赫連。
「不是,隔壁老王是醫生。」赫連回應:「但那個大頭怪嬰降生的時候,我就在產房外面。」
我的判斷果然是正確的,我正想再跟赫連打聽打聽,群里就開始沸騰。
「我真的快要瘋了,白天睡覺,晚上熬夜,我的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是啊是啊,我的皮膚已經變的很糟糕了,心塞。」
群里的人在抱怨,高富帥還有丁靈的話是最多的,他們打字又快,一行一行的刷屏。通過群里的交談,我漸漸的看出一些端倪。這些人都被噩夢困擾著,已經出現了神經衰弱的前兆,聚集在一起,就是為了合力想辦法來對抗或者化解那個詭異的噩夢。
我本來對這些陌生人是充滿了懷疑和不信任的,但是知道了這個群成員的遭遇之後,那種陌生和懷疑一下子消減了許多,或許是同病相憐的原因,我很理解被那個足以逼瘋人的噩夢困擾的痛苦。
「我們的人已經齊了。」赫連沉默了很久,終於開始發言。
在我進群之前,這些人肯定有過交流,只不過我是最後一個進來的,為了讓我明白事情的經過,在赫連的帶動下,這些人相互補充,又把過程複述了一遍。
一直到這時候,我才知道大頭怪嬰的真正來歷。
這個事情發生的時間,要追溯到十月十二號,當天早上,一個待產的孕婦來到第一人民醫院。這其實是個很正常的事,但這個孕婦來到醫院以後,就不斷的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異常。
整個產科的人莫名其妙的感覺煩躁,有人時常都能聽見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的哭聲和笑聲,幾個前幾天臨盆出生的嬰兒,和發羊癲瘋一樣,同時休克。整個產科頓時亂成一團糟,當時恰好有個陽城日報的記者在場,這件事就被當成一條小新聞,刊登到十三號的晨刊民生版塊中。
最後,十三號那天的報紙被緊急追回了,只有一小部分流出,但看到報紙的人,絕大部分都不知情,所以,這條新聞以及後續情況沒有引起傳言和騷動。
接下來,那個待產的孕婦在晚上八點左右分娩。
分娩的同時,產房裡就和砸鍋一樣,醫生和護士的驚叫里,夾雜着一陣彷彿不像人一般的叫聲。整個產房到處都是血,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的頸部大動脈被撕裂致死。
我心裏明白,這就是大頭怪嬰降生的經過,這個怪異的嬰兒從出生開始,就帶來一場血光之災。
在場的人都被嚇住了,緊急轉移了產科里的大人和孩子,然後封了產科的門,等待救援。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丁靈插嘴發言:「過道上都是血,那個……那個頭大大的小baby,在血里爬來爬去……」
「你真有母性和愛心,那也算小baby?」高富帥發了一個嘔吐的表情:「我現在想想它的樣子,就忍不住要吐。」
和我預想的差不多,赫連,白領,隔壁老王,高富帥,丁靈,這幾個人先後親眼目睹過大頭怪嬰。
後來,醫院裏先是來了警車,在產科附近圍觀的人都被驅散了,所以後面的情況,他們都不知道。
我隱約感覺到,大頭怪嬰不是police能搞定的,由此,那兩輛卸了拍照的帕薩特里的人,浮現在腦海。
大頭怪嬰肯定是這幾個人弄死的,然後毫不猶豫的直接把怪嬰的屍體拉到火葬場焚燒。
大概的過程就是這樣,過程雖然比較清晰,但我一直都在想,什麼樣的人,才能生下大頭怪嬰?我的腦洞大開,甚至把污染輻射,近親結婚,基因突變這些因素都考慮在內了,可就算基因突變,生下來怪胎,也就是個怪胎而已,不可能像大頭怪嬰那樣,充滿了恐怖,還有魔性。
我琢磨著,既然自己被牽扯進來,那就乾脆刨根問底,深挖,朝祖墳上挖。所以趁著群里人相互討論的時候,我又私聊了赫連。
「有大頭怪嬰父母的信息嗎?」
「生下怪嬰的孕婦,叫李斯雲,是我一個朋友。」
「那怪嬰的父親呢?你知道是誰嗎?」
「我知道。」赫連打了三個字,然後就沉默了,雖然只是用微信交流,但我能感覺的出,赫連應該是個穩重的人,就算文字交流,也要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肯把字打出來,他至少沉默了一分鐘時間,才接着說:「我知道他,但沒親眼見過。」
「他是什麼人?」
赫連又沉默了,不知道在考慮什麼,過了好半天,我才看到手機螢幕上顯示出他的回答。
「他很可能不是人。」
「這話怎麼說?」我看到赫連發來的信息,腦子一暈,暫時就反應不過來了。
不過就是一秒鐘時間,我自然而然的產生了一個想法,大頭怪嬰那麼詭異,如果沒有極其特殊的情況,正常人肯定孕育不出這樣的怪胎。
我怕赫連不肯把所有的實情告訴我,因為畢竟彼此之間是陌生人,以前從來沒有打過任何交道,就像我心裏存在着疑慮一樣,別人對我估計也不會百分之百的信任。
「這件事,一句話說不清楚,如果你有興趣,明天我們可以見面談一談。」
「好。」我沒怎麼猶豫,赫連肯說出一些事件背後的秘密,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儘管已經快凌晨三點了,但群里這幫生物鐘完全顛倒的人刷屏刷的不亦樂乎,我沒有心情和他們閒扯淡,一直都在默默的看。
我不說話,心裏的懷疑卻沒有停止,夢對一個人來說,應該算是絕對的隱私,如果做夢的人不泄露出去,沒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夢境。想着想着,我就對這個群的群主產生了興趣。
這個叫影子的群主很神秘,包括最早進群的赫連也不知道影子的身份。就是這個不知身份的影子,洞悉群里其他六個人曾經做過的夢。
他是怎麼知道的?
我就默默的看着群里人聊東聊西,一直看到天亮。天一亮,正常人都該起床了,這些人卻該睡覺。我急於知道赫連將要透露的內幕,睡了一上午,午飯剛過,就匆匆起床,趕到跟赫連約定的地點。
我們約好的地方是一個茶樓,我早到了十分鐘,坐下來等。兩點準點的時候,赫連到了,和約定的時間一分鐘都不差。
他大概有三十二三歲的年紀,瘦但是很精神,臉龐稜角分明,皮膚是古銅色的。他非常健康,可能經常鍛鍊,透過緊身的黑色毛衣,能看到他凸起的胸肌和腹肌。他有點黑,但五官俊朗,左眼的眼角到額頭,有一道已經癒合很久卻微微凸顯的疤。
這道疤讓赫連看起來充滿了野性,還有隱隱的霸氣。他很酷,坐在我對面,沒有像正常人初次見面那樣言語寒暄,整個人就像肥皂劇裏面那種冷麵大叔。
我嘗試着跟他建立一種良好的溝通氛圍,赫連在微信上話就不多,現實里更是惜字如金,好像多說一個字就會浪費卡路里。不過他的語言精簡明了,幾句話就讓我知道了大頭怪嬰母親的情況。
那個叫李斯雲的女人是本地一個單身女人,二十八歲,做酒店一次性衞浴產品生意,性格有點怪異孤僻,因為性格的原因,李斯雲的朋友不多,不過我算看出來了,這種性格的女人,跟赫連這樣酷酷的男人,應該是比較對眼的。
大頭怪嬰這件事情之前一個月左右,李斯雲約赫連吃了頓飯,剛一見面,赫連就感覺李斯雲有些不對頭,憔悴不堪,而且彷彿神經過敏,勺子和盤子無意間碰撞發出的輕響,都能讓她渾身發抖。
赫連就知道,李斯雲估計是出了什麼事,她很可能承受不住打擊,才找赫連來訴苦的。
果然,在赫連耐心的詢問下,李斯雲慢慢說出了事情經過。她的確出了事,而且是正常人很難想像的一件事。
連着幾天,李斯雲不斷的做夢,她夢見自己在一個黑暗的囚室裏面,躺在冰冷的硬板床上。每次當囚室外面傳來零點的鐘聲時,就會有一個幽靈一樣的男人,壓在李斯雲身上,圖謀不軌。
雖然是在夢裡,但那夢境也真實到了極點,真實到李斯雲甚至分辨不出這是夢,還是現實。她激烈的反抗,那個幽靈一樣的人就死死按住李斯雲的雙手,讓她動彈不得。
幽靈每次得逞以後,會悄無聲息的離開,之後,李斯雲就猛然驚醒。
可能是夢太真實的原因,連着幾天下來,李斯雲吃不消了,精神受到了很嚴重的刺激。
當時,赫連安慰她,說那只是個夢而已,真有必要,可以吃一點安眠藥。
不說則已,赫連一安慰,李斯雲當時就哭了,她的樣子很怕,捂著嘴,不敢哭出聲。她跟赫連說,那肯定不是一個夢。
她讓赫連看了自己雙手的手腕,李斯雲的手腕上,有一道因為強力的擠壓而產生的輕微淤痕。
因為李斯雲的情緒很不穩定,所以赫連在很短的時間裏判斷不出李斯雲的講述是否屬實,而且一個情緒極其波動又神經過敏的人,沒準會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下產生並不存在的幻覺。
赫連不動聲色,繼續觀察李斯雲,隨後,他的心裏也產生了一絲莫名其妙的驚恐,因為他發現,李斯雲可能沒有說謊。
一個正常人,尤其是一個獨居的女人遇到這種事情,就徹底失措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被逼到無路可走的地步,李斯雲也不會把這事講給赫連聽。
赫連當時還沒有被大頭怪嬰帶來的噩夢困擾,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幫李斯雲出了一個主意。既然李斯雲懷疑那個亦真亦幻的夢,就要知道這個夢究竟是真的,或是假的。赫連不能親自陪着李斯雲,如果多一個人,「夢」可能會改變,也可能會消失。
他建議李斯雲睡覺之前,在臥室一個隱蔽的角落裡放置一台DV,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這一夜之間臥室里所發生的一切全部真實的攝製記錄下來。
「她照做了?」我忍不住問赫連。
「做了。」
李斯雲雖然按著赫連的建議去做了,但這之後,李斯雲突然又沉寂了,沒有主動跟赫連聯繫。赫連問過李斯雲,電話里問的,李斯雲說沒事。
過了不到一個月,有一天早上,李斯雲突然打電話給赫連,僅從電話里,赫連就聽出她的語氣不對,所以立即趕到李斯雲家裡。
見到李斯雲的時候,赫連很震驚,相隔不到一個月時間,李斯雲的肚子詭異的隆起,她的狀態很不好,赫連把她送到了醫院。到醫院以後,醫生毫不猶豫的診斷,李斯雲將要分娩了。
這一天,就是十月十二號。
後面的事,赫連不說我也知道,李斯雲生下了那個大頭怪嬰,在醫院掀起一場不小的波瀾。
「這個李斯雲呢?她現在怎麼樣?」
「她死了。」
我有一種淡淡的,而且形容不出來的悲哀。在這個事情里,人的生命好像變的無足輕重,一個生命如同一個氣泡,隨時都會崩裂消失。
赫連不是一個愛說話的人,講到這裏,我們都沉默了。過了一會兒,我試探著問他:「李斯雲拍攝時用的那台DV,還在嗎?如果可以的話,我能不能看看裏面的內容?」
「可以。」赫連從身上掏出一個U盤,輕輕的推過來:「看完之後,把視頻刪除,不要保留。」
「你信我?」我接過U盤,有一點意外,本來我以為要跟赫連討價還價半天,他才會把這些秘密透露給我。
「我們要一起對付那個噩夢。」赫連淡淡的看了看我,說:「而且我能感覺出,你是一個會思考的人。」
我暫時跟赫連道別,帶着U盤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迫不及待的開始觀看U盤裡的內容。
可以說,U盤裡的內容是我能親眼目睹的這個事情最早的起源點,所以我看的非常認真。DV以一個穩定的角度,把臥室里發生的一切全部清晰的記錄了下來。
在視頻里,李斯雲洗漱之後,躺到了臥室的床上。很顯然,她很恐慌,感覺到極度的不安,身體在被子下面縮成一團,不停的朝DV所在的方向看。
過了最多十幾分鐘,李斯雲就在這種狀態下昏沉沉的睡去了。幽暗又空蕩的臥室里陷入一片死一般的沉寂中。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任何動靜。
一直看到這兒,視頻的內容依然是正常的,畫面中的李斯雲就好像這城市裡無數個在深夜進入熟睡的人。
當時間不知不覺中流動到凌晨零點的時候,平靜的畫面突然像水波紋那樣輕輕抖動了一下,DV前的整個臥室彷彿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扭曲著。
這種扭曲只持續了一秒,畫面隨後就恢復正常。但這短短一秒鐘的時間裏,我一下子就感覺到一股陰森森的氣息,從面前的螢幕里透射出來。我睜大了眼睛,死死的盯着螢幕,唯恐錯過哪怕最細微的細節。
驟然間,我覺得頭皮猛然一緊。李斯雲的床邊,不知道什麼時候多出一雙鞋。
一雙在現實社會中完全絕跡的草鞋,整整齊齊的擺在李斯雲的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