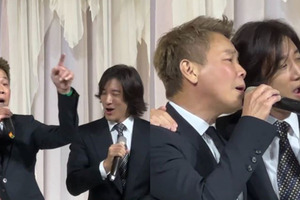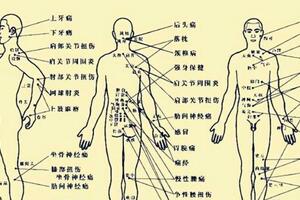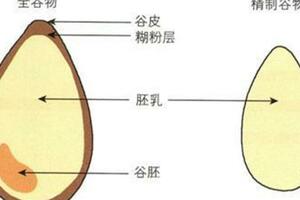譯林出版社近日推出了《新藥的故事3》,這是新藥研發一線科學家、知名科普作家梁貴柏傾力創作的醫藥科普書系「新藥的故事」的第三部作品,延續前兩本的通俗風格,繼續用平實的語言和生動的敘述,細膩講述生命科學前沿的動人故事,呈現人類醫藥事業的奮進與攀登。
南美部落的狩獵毒箭,如何為現代急救做出貢獻?美容護膚的綠黏土,怎樣成為治療腹瀉的基礎藥?大蜥蜴吉拉怪獸,竟給糖尿病治療帶來新的曙光?《新藥的故事3》圍繞著九種扭轉頑疾困局的重磅新藥,講述了九個峰迴路轉的研發幕後故事。從銀屑病、糖尿病到肢端肥大症、肺纖維化,從病理研究、藥物研發到臨床試驗、上市審批,本書聚焦講述實驗室、科學家和製藥團隊經年累月的探索,帶領讀者一同見證人類挑戰病痛的曲折歷史。
這是一本知識豐富的藥學科普書,同時也是一部有趣好看的醫學故事集。這得益於作者的「跨界」功底,既是在新藥研發一線奮鬥多年的科學家,又是多年來孜孜不倦於為廣大普通讀者奉上科普知識的作家。鍾南山院士曾這樣評價梁貴柏:「作為一名理科出身的資深科學家,作者的文字素養可圈可點,尤其是在解釋新藥研發的科技背景時,並不令人感到艱深和乏味,而是有一種豁然開朗的體驗。」
梁貴柏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化學系有機化學專業,20世紀80年代後期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留學,並獲博士學位,在康奈爾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畢業後,梁貴柏在默沙東實驗室工作多年,對西格列汀的研發做出過重要貢獻,長期致力於中美醫藥界的交流與合作,積極推動中國醫藥健康事業的發展。
近年來,梁博士一邊繼續新藥研發工作,一邊耕耘他的科普創作園地,堅持以明白曉暢的文字、清晰明朗的結構、深入淺出的講述,既為醫藥業內人士,也為廣大普通讀者呈現藥物研發背後那些曲折的探索、艱難的戰鬥,分享製藥人在失敗與勝利中的堅持不懈、人類醫學為對抗疾病發起的一場又一場科學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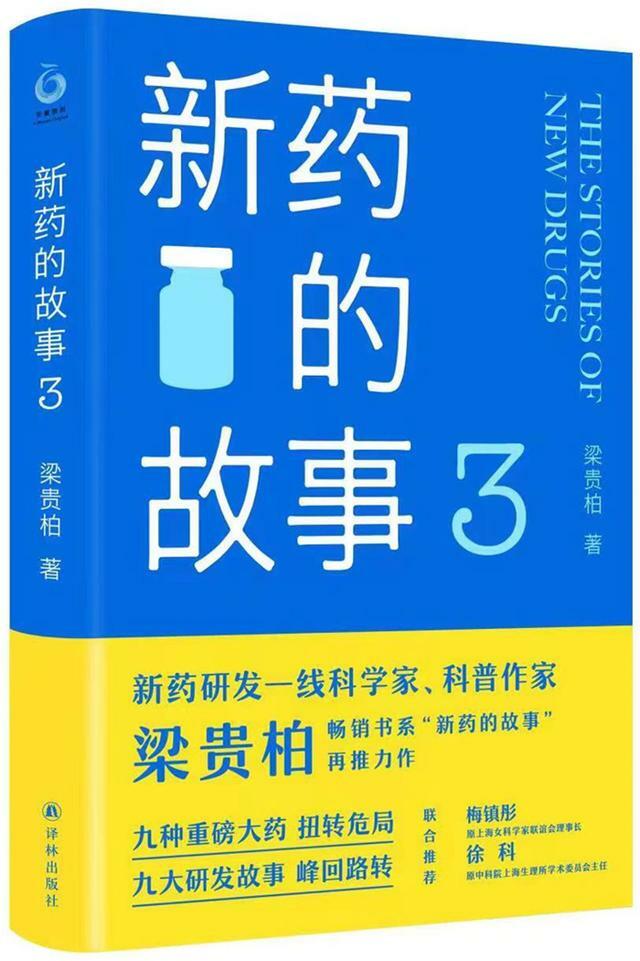
《新藥的故事3》
梁貴柏 著
譯林出版社2022年9月版
後 記
在過去的一年裡,知道我還在繼續寫「新藥的故事」系列的第三部,很多朋友的第一反應是:真有這麼多故事可以寫嗎?跟以前的兩本有啥不同?
第一個問題很容易回答:真有!
如果大家確實很想了解健康與疾病、科研與製藥的故事,一直有這個需求,我這輩子是寫不完的。原因很簡單:基礎生命科學的研究成果才剛剛為我們揭開了健康與疾病的冰山一角,還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探索,去挖掘,去嘗試。每一次成功都將是一個值得撰寫的故事。
我自己進入製藥界是在2000年之前。那時,由全球許多科學家共同參與的人類基因組項目已經進入了關鍵階段,整個生命科學領域和製藥工業界都翹首以待。一位當時快要退休的老前輩很興奮地告訴我:你現在進入製藥公司是幸運的,因為人類基因組項目完成之後,現代製藥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你們這一代製藥人是可以大有作為的。2003年4月,歷時20多年的人類基因組項目終於完成了,我們可以從中讀出人類的所有基因和它們所編碼的蛋白質。對於製藥人來說,這可是夢想成真的時刻。第二天有多少製藥人是哼著小曲去上班的我不知道,但是人類基因圖譜並沒有在一夜之間顛覆我們的認知,也沒有讓這位老前輩預告的嶄新時代一下子閃亮登場,而是像以往的很多重大發明和發現那樣,慢慢地滲透到了製藥科學的各個角落。
最先獲益的是直接與基因序列相關的遺傳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
現在我們可以精準定位基因變異,很多遺傳病都可以在很早期,甚至產前做基本無創的精準診斷。我不止一次講過,精準醫療的基礎是精準診斷。如果我們不知道兩個患者的不同之處,「精準」又從何談起呢?現在我們有了人類基因圖譜,再加上準確、快捷和廉價的基因測序,就可以精準地診斷尚未出生的患兒哪一條染色體上的哪一個位點出現了怎樣的變異。從相關蛋白質的表達,到致病基因的修復和調控;從生物工程的替代酶(見《新藥的故事2》第九章《追根尋源戈謝病,對症下藥思而贊》),到反義寡核苷酸的藥物(見本書第一章《反義終成正果:諾西那生鈉的故事》)……經常有朋友問我到底什麼是精準醫藥學?這就是。不是未來,就在當下。
人體基因組項目的完成並沒有把新藥研發變得容易,它只是解開了生命奧秘的又一層「面紗」。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現象,就是過去十幾年裡各種「epi-」製藥項目,比如「epi-genetics」(表觀遺傳學)的製藥項目、「epi-transcriptomics」(表觀轉錄學)的製藥項目,以及專攻這些靶點的生物技術公司的湧現。我們把希臘語的前綴「epi-」翻譯成「表觀」,意思是不涉及內在的DNA或RNA序列的變化,但又是可遺傳的表型變化。這是健康與疾病的又一個前沿領域。
說我們只揭開了健康與疾病的冰山一角是一點都不為過的,而我寫的這些故事就是這露出水面的一角冰山上的幾個晶瑩的亮點。
第二個問題不太容易回答:有很多不同之處,也有不少相同之處。
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藥物、不同的研發過程、不同的患者體驗……聽上去好像都不相同;但是,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同樣的科學好奇心、同樣的患者無助與醫者仁心、同樣的臨床需求和市場監管、同樣的新希望……
現代研發完全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新藥的成功、新療法的建立總是在基礎研究的突破之後,這應該是它們之間最重要的相同之處。即便是像「蒙脫石散」這樣從天然黏土礦物中開發出來的藥物,也需要科學研究的支持,積累大量可靠的實驗數據,同時還要保證生產工藝的嚴格、可重複,方能惠及全球的患者。一位資深的製藥工藝負責人曾經當面問過我:「你願意吃次品藥物嗎?可以便宜不少哦。」我堅決地搖頭說不願意。你呢?
生物工程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給製藥工業提供了極具多樣性的研發平台,這也許是它們之間最顯著的不同之處。雖然以化學合成技術為基礎的小分子藥物依然有著廣闊的前景,但是以各種新型生物工程技術為平台的藥物研發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引領著新的潮流。就拿反義寡核苷酸的技術平台來說,它經歷了幾十年的起起落落,承受著長久的寂寞,終於在遺傳病的基因調控上找了自己的位置,修成正果。我們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反義寡核苷酸藥物去填補眾多尚未滿足的臨床需求。再比如與傳統藥物截然相反的「解藥」這個概念,也已經不再是武俠小說作家的想像,而是切切實實的臨床需求。無論是能在短時間內恢復凝血功能的依達賽珠單抗(見本書第六章《血液的「兩面性」:血栓與抗凝》),還是麻醉手術後醒來能恢復肌肉功能的舒更葡糖鈉(見本書第九章《真實世界裡的「十香軟筋散」及其解藥舒更葡糖鈉》),都在它們各自特殊的醫藥領域裡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者:梁貴柏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