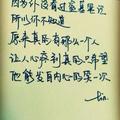我和老公雖不算青梅竹馬,但大學整整四年都是同班,彼此應該算很了解,也曾愛得一塌糊塗。
記得1986年熱戀時,心裡堅定不移地想,愛他,就是他身上的一根肋骨。他也跟我不分彼此。
有時,我們抱在一起好久,像被萬能膠粘成一塊複合木板,誰也放不開手。
畢業後,我分配在開封檢察院,他分配在洛陽市一個區的城管辦。都是吃國家飯的,算是「門當戶對」,讓人羨慕得掉睫毛。
那時候窮,工資也低,一年才見兩三次面,我們被相思折磨得半死不活,我們每天一封情書,有時整整一天什麼事也沒做,只是想他,一口氣給他寫三四封信,每封信都寫得婆婆媽媽,用去半本信箋紙。
有一次,他來看我,我義無反顧地把一切交給他。我們沒有拍婚紗照,沒有辦喜酒,沒有告知親朋好友,那晚,他吻著我入睡,天亮後我又被他吻醒。我的淚花從傍晚閃爍到第二天太陽照進半個宿舍。
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比他更好的男人。
結婚後,我們還是沒有調到一起,但我們的「來往」非常頻繁,工資都用來兩地跑了。他來看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瘋狂地吻我,每當這時候,我都幸福得想死在他懷裡,永遠不要醒來。
然而,這種感覺卻不能永遠。
第二年,我們有了一個女兒,婆婆來開封幫我照顧她。我的精力和感情開始轉向女兒,而且幾乎是全部給了她。
老公沒有那麼頻繁地來回跑了。我們昔日的激情像泉水,一點一點地流淌掉,而天卻不下雨,庫存的激情越來越少。
有一天,當他躺在我身邊的時候,我竟感覺跟他有點陌生。好像是幾年前認識的一位好友。
情人節,看到姑娘們捧著一束一束大紅玫瑰,我問:怎麼不給我買一束?他卻笑著說:都孩子她媽了,還那麼幼稚?
我表情自然,心裡卻感覺愛情少了很多味道。
我是個不甘寂寞的女人,1995年,我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很順利地過了關,拿到了律師資格證。
我想憑自己的本事掙錢。我對不義之財嗤之以鼻,曾經有人送給我一筐家鄉雞蛋,我都趕緊連夜全部交給領導。
我覺得夫妻兩地跑實在不像夫妻,拿到律師資格證不久,我便決定到深圳闖。當時只是想來掙點錢,回去買一套好一點的房子。但來深圳後,我就不想回去了,跟很多闖深圳的人一樣,喜歡這座年輕而不相信眼淚的城市。
在深圳,我出乎意料地順利,進了一家大型企業做法律顧問,高薪而清閑,業餘自己也做點業務。
我多次動員他來深圳,他堅決不肯來,怕失去工作。
1997年年初,我在福田一處高尚住宅區供了一套房子。我是個很講究居住品位的人,房子都按我的構思進行設計裝修。每天早上,我都會在陽台喝一杯咖啡,翻翻時尚雜誌,透過陽台欄杆看遠處的風景,然後把自己打扮得很得體,才去上班。
我從不帶男人來家裡,不是特別親密的女人,或者不是高雅的女友,我也不會帶來家裡。我覺得,家是很隱私的地方,是很有品位的場所,必須「往來無白丁」。
那段日子,我孤單卻很舒適。
雖然我喜歡清靜,但因為一個人在深圳,交的朋友還是不少。其中,林就是我比較信任的朋友。他是羅湖區一名普通警察,年輕而有才氣。
199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一位大款老鄉在蛇口五星級酒店———南海酒店請我吃飯,說要跟我談一個經濟案。
老鄉是廣州一家中型企業的老闆,在深圳有不少業務,我欣然前往。
也許是他知道我長期一個人待在深圳,再加上「孤男寡女」包了一個房間,酒過三巡之後,他突然說起了瘋話:「你這麼性感,真不忍心讓你守活寡。」說著就來抓我的手。
我拚命掙脫開來。
本以為拒絕他後,他會安分下來,沒想到他卻趁著酒勁,把上衣脫了,露出了滿身的強盜肌肉和野人一樣的胸毛,並靠過來想抱我。
我嚇得連滾帶爬躲進了包間里的洗手間。
我有點醉,也有點清醒。他來敲門,我把門反鎖得緊緊的,不敢打開。我拚命地洗手,覺得手被他摸過,很臟。洗完後,我在裡面哭,不敢出來。
突然,我想起了林。林是警察,我想,如果讓他來接我安全的。我給林打電話,胡言亂語地說要請他吃飯,讓他到蛇口南海酒店來,並故意大聲地跟他說話,想讓大款老鄉聽到。
儘管大款不知道要來的人是個警察,但他馬上對著門縫說:出來吧,我穿好衣服了,都怪我剛才喝多了,對不起。
等到林到了酒店門口給我打電話,我才敢開門出來。林走到包房門口,我拉著林的手,一直跑了有一公里遠,然後蹲在一處牆角哭,把林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突然不知從哪來的勇氣,把他拉住了。我把他抱在胸前,輕輕地抽泣。
那一夜,我擁有了林。我一夜沒睡,愛得瘋狂,又自責得無地自容。
以後,我和林順理成章地成了情人。但我的良心一直感到不安。我給丈夫下最後通牒:如果再不來深圳,只好分手。